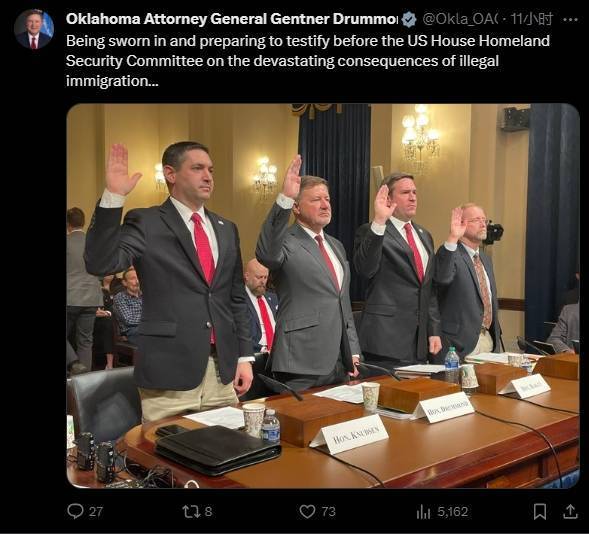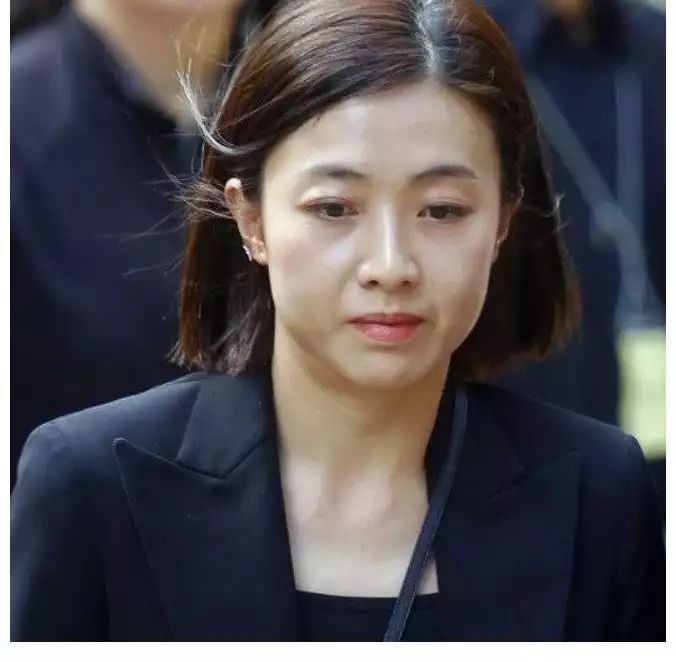系列专题|华夏文明的信仰共同体--洪洞大槐树(二)
- 娱乐
- 2023-03-03
- 148
洪洞大槐树移民促使华夏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发生交流、碰撞、沟通、融合,文化之间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并产生深远意义。
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的影响
重塑恢复民族传统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华文明的传播中,社会影响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而重塑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恢复民族传统文化,无疑是最重要最深远的方面。
元朝在当时被视作夷狄,是为中原民族所轻视的野蛮民族,它能入主中原,对中原民族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就这样写道:“自古君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纲常伦理道德不再是唯一的主流文化,汉文化的正统地位被破坏殆尽。
山西拥有悠久醇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晋南作为尧舜故地,是汉民族文化、伦理道德的发源地,大量古槐移民的迁播,必定会将儒家传统文化和公共伦理道德传播到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会大大促进礼教的普及。
在大槐树移民迁居地有不少纪念性的标志和建筑,表达了浓浓的怀乡念祖之情,如河南省博爱县刘家祠堂的匾额为“派衍洪洞”,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是:“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武陟县大陶村孙氏神位的对联是:“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偃师市韩寨村赵氏家谱载:“始祖兄弟四人,名经、营、槐、显。”“念新造之艰窘,伯与仲故谓经,而为营。恐故乡之遗忘,叔与季则谓槐,而为显(乡谐音)。”连起来即为“经营槐乡”。因当时有兄弟几人为了同居一村而改为异姓者,至今仍有“回、霍、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宗、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的说法。
水流万里总思源,树高千尺不忘根。大槐树移民无刻不在思念故土,梦绕魂牵大槐树,将思念之情写在家谱中,刻在祠堂墙碑上,收入诗文歌赋里。例如山东菏泽移民写的《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戒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为了看到槐树,留住槐根,寄托思念之情,不少移民新村都植“立村槐”,给新开的店铺取名“老槐店”。
以移民姓氏命名地名村落
这样的例子在河南、山东、安徽、北京等地比比皆是。例如在鲁西南一带就有大约一半的村庄是在明代山西移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上世纪80年代山东滕县地名办公室的调查,全县现有1223个自然村,明代建村的就有687个,占村庄总数的54.3%。定陶县1050个村庄中,有388个村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迁来的。北京大兴县地名办公室调查,全县526个自然村,有110个是因洪洞移民设置的,而以移民姓名作村氏的就有45个。在北京市郊区,还有许多以移民原籍命名的村庄,如赵城营、长子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等等,寄托了大槐树移民浓浓的故乡情思,通过移民,人口的生存空间得到了合理的分布,中华民族的族群结构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