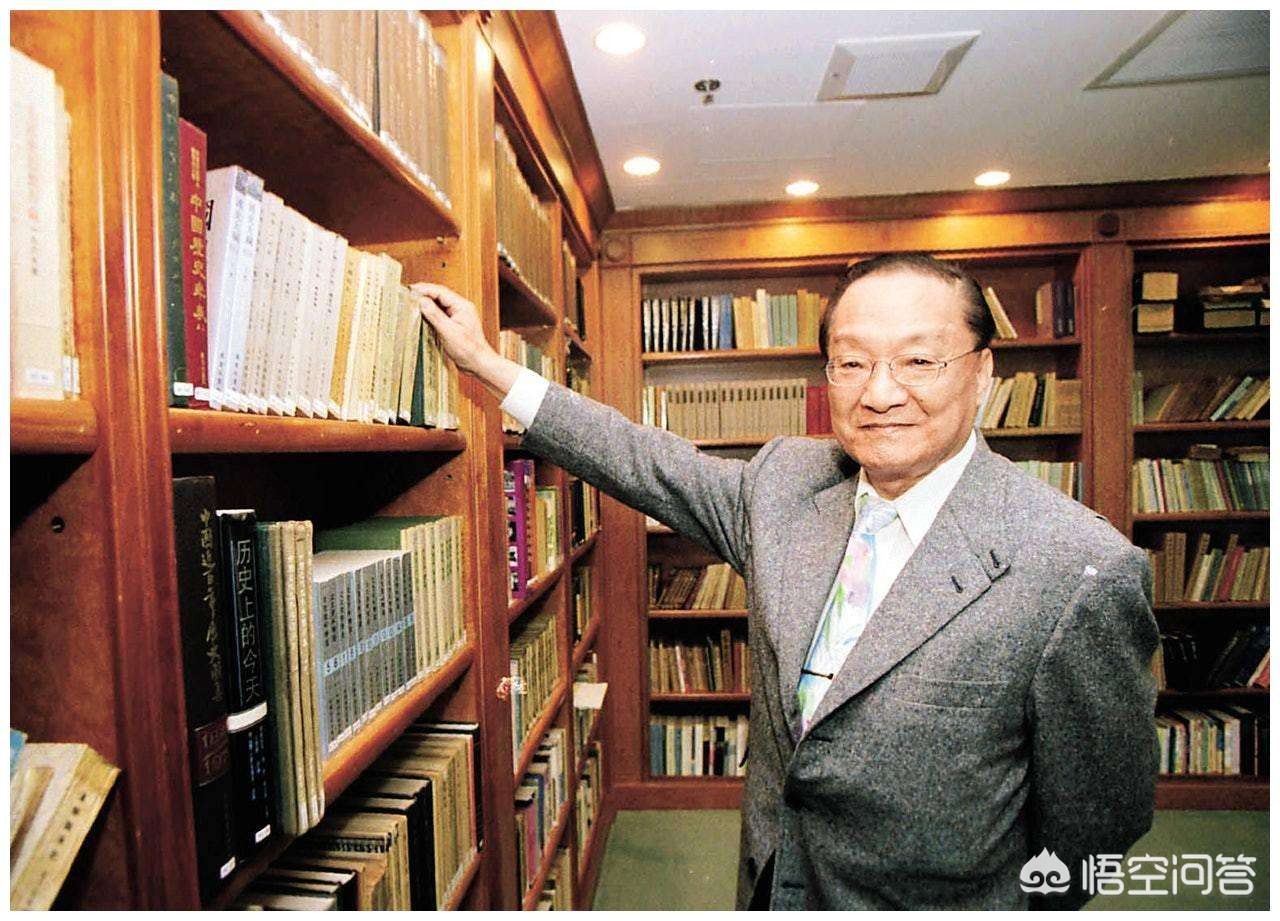[王蒙文学部·环渤海文化]小说:路在哪里|潘瑜(内蒙古)
- 娱乐
- 2023-03-06
- 129
总第(5597)期 |总编:觉斓|主编:铁骑
原创诗歌|配图: 网络
路在何方
潘瑜
一
小院里,凄惋、低沉的唢呐声,伴随着一位少年男子断断续续的哭泣声,迷散在烟雾缭绕、人声嘈杂的空气中。
范解放跪在停放棺材的灵台前,身着白色孝服,腰系三尺麻绳,两眼泪汪汪地用嘶哑的声音哭诉着:“爹,您丢下我怎么办呀--”他那沉痛的哭声震撼着前来奔丧的男女老少,都纷纷抹着眼泪,为这个可怜、孤单的孩子担心。
一股黑风从昏暗的天空中吹下来,吹灭了灵台前的长明灯,吹起地上的纸钱,漫天飞舞,人们惊慌地跑出大院。
清晨,太阳刚从东山背后升起来,小羊倌范解放早已领着羊群走出村庄,在一个平坦的大草滩上停下来。
绿油油的小草连成一片,伸向远方,仿佛是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羊群在草滩上慢慢地移动着,像一朵朵白云,又似颗颗晶莹的珍珠。微风吹来,带着百灵鸟儿的歌声,在淡蓝色的天空中飘荡。宁静的草滩,暖融融的阳光,使解放的困意一阵阵地袭来,他长长地吸了口新鲜空气,觉得精神了许多,在一小土丘上坐下来,望着天边起伏不平的山峦遐想....
夏天的天空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朗朗晴天,忽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解放站起来,“呸”唾了口唾沫,把食指和中指放在嘴里,使劲一吹:“嘘一一”长长地一声。所有的羊都跟着他直奔前边的土坡下拥在一起,他与领头的大公羊偎依着。狂风撕乱他的头发和衣裳,使劲要他与羊群分开,雨丝抽打着他的脸庞和后背,他浑身哆嗦着,恐惧地结结巴巴对大公羊说:“老大......你......可......不能......跑.....你......一跑......你......一跑......就......就.....乱......乱了.....了......”大公羊“咩-一咩-一-咩--”地叫着,紧紧挨住解放挺在风雨中。
雨过天晴,太阳恢复了先前的灿烂。东方的天空中,现出绚丽的七色彩虹,解放的羊又散开了,踏着浅浅的雨水,高兴地啃着挂满水珠的鲜草,还不时地叫着,仿佛感谢解放对它们的关心。
解放如释重负地站起来,抖掉头上、身上的水珠,拉开裤子,站在草滩上舒坦地尿完,甩甩湿漉漉的头发,坐在石头上,从胸前掏出一本被雨水浸湿的破旧连环画,聚精会神地看着。
冬天到了。解放穿着单薄的短袖棉袄和母亲做的牛身子布鞋,站在干枯的草滩上,吆喝着羊群。天空飘飘扬扬落下鹅毛大雪,白茫茫地覆盖着大地。呼呼的北风,扬起雪花遮天盖地狂飞。解放的破棉帽下面,忽闪着的睫毛上都挂满了雪粒。羊群炸开了。任解放把手指放在嘴里怎样“嘘--嘘一-”响亮地吹着,大公羊都不听话。他的嘴里不住地呼出结冰的热气。脚下踏着厚厚的雪层,不停地追羊,啪——”声响鞭,抽在大公羊身上,大公羊停住了,其他的羊也跟着围成一团。
夜幕罩住草滩,风雪仍在飞舞。解放不知疲倦地把羊挨家挨户送走,才拖着疲惫、瘦长的身子走回家。
“儿呀,可把你冻坏了。”母亲心痛地说。
“不不不......冷冷冷......不不不......”解放的牙齿不住地上下磕碰着。
光阴流逝。二月的春风送来使解放兴奋不已的消息--全国恢复高考了。他仿佛是草滩上无人理睬的小草遇见甜甜的甘霖,一边放羊,一边啃着高考的书本。那一天,一只母羊下羔了,“咩一一咩”地在羊群中叫着,可解放怎么也没听见老母羊惊恐的叫声。很久,他在一张废纸上解完书中的难题,抬起头来。忽然看见老母羊望着他不住地叫。他走过去一看,啊,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被踩死了。他蹲下来撕着自己的头发,抱住老母羊说:“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呀。”可老母羊的主人不答应,必须让赔偿。
除夕夜,爆竹在空中爆响,快乐的锣鼓声在街心敲打。几个同年好友约解放出去熬年、玩耍,可他笑着说:"你们去吧,我要在家里接神。”三炷清香,冒着细细的清烟,萦绕在灶神位的上空;两支红蜡,流着道道眼泪照亮神位的前边。解放就伏在这里的柜台上,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拿出书本,喃喃地念着。
他终于考上大学了,可难处也来了。
那天晚上,年迈的母亲坐在炕沿上,用手掰着玉米棒,嚅动着嘴唇说:“儿呀,放羊的工钱人家都给了,可还不够你的学费......”
解放听了母亲的话,心里酸酸地难受。是呀,自打父亲死后,母亲为使独生儿子少受点苦,整天吃力地迈着缠过的小脚,背着沉重的高粱杆,在田地里转着。他这样走了,留下孤苦的老娘,是不是不孝的儿子?他低低地对母亲说:“妈,要不我别上学了,再放羊吧。”
“你要是真孝敬妈,就走吧。给你爹争口气,你明儿个去你姑妈家走一趟,兴许你姑妈能借给些钱。”母亲认真地对解放说。
看见姑妈那低矮的院墙、破旧的小屋,解放的心也沉重起来。他知道姑妈也穷得叮当响。他软软的双腿慢慢地迈着,来到姑妈的门前。
姑妈从门里出来拉着解放的手笑着说:“解放,好久没来看姑妈了,快进屋。”
“姑妈。”解放长长地叫了一声,竟“扑通”跪在姑妈的面前
“侄儿,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姑妈慌了,拉着解放的手说。
“姑妈---你答应侄儿一件事,我就起来。”“啥事?姑妈答应,快起来吧。"
“姑妈,我考上大学啦,凑不够钱,您能帮我一回吗?解放仰着脸哀求地说。
姑妈扶起他,说:“解放,甭怕,姑妈砸锅卖铁也要帮你。”
东去的列车飞驶在广阔的原野上。
解放站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门里,听着火车发出欢快的咣当声,仿佛有节奏地叫着:范解放、范解放......解放那消瘦的脸庞,仍挂着放羊时的沙尘。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服穿在身上,虽然满是补丁,可显得格外精神;一双从来没有擦过鞋油的大皮鞋,虽露出白碴子,可踏着车厢地板的声音,特别响亮;一双大大的眼睛望着窗外,闪着兴奋的光芒。窗外,巍峨的山峰迎面扑来,几只苍鹰在天空中盘旋着、搏击着,又向山那边飞去了。他的心从来没有这样自由和舒畅,仿佛也随着这行驶的列车飞向远方。“有奔头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呸!”他朝火车的地板上重重地唾了口唾沫。
“同志,请别往地上吐唾沫。”站在身旁一位背着背包的高个子姑娘不满地说
“啊?俺在村里就这样。”解放回过头来看着她,振振有词地说。
二
四年后。宁远湖畔
夕阳的余辉照着静静的湖面,熠熠生辉;清风吹动着微波;粼粼闪光。一对对即将毕业的青年人坐在月牙形的小船上开心地唱着,难舍难分地拥着。解放坐在曾和未婚妻长吻过的地方,拨开飘在眼前的杨柳枝条,望着弯弯曲曲由石子儿铺成的小路。不一会儿,一位身穿红色连衣裙,梳着长长小辫儿的高个子姑娘向他走来。她就是解放在四年前火车上偶遇的姑娘,现在是同班同学,未婚妻刘慧敏。
慧敏。”解放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
慧敏噘着红红的小嘴,满脸忧伤地走到他跟前。
怎么,还生我的气?”解放笑着,拉住慧敏的手,想拥抱她。
慧敏支开解放的手,长久地在垂柳树下沉默着。
“你,怎么不说话?
“解放,咱们…”音
“咱们怎么啦?”解放急着问。
“分手…
“啊?为什么?”
我爸、妈不同意,说你……”
说我啥?说我穷,没地位,门不当,户不对,是不是
解放双手摇着慧敏的肩膀大声问。
“嗯”
“那你的态度呢?”
“我拗不过爸、妈......"
空气仿佛凝固了,解放蹲在草坪上,双手托着头,失神地望着灯光闪烁的湖心。
“解放,我对不住你。”慧敏擦着眼泪说。
解放的耳朵里呼呼地响着,像有股无名的火焰就要蹦出来。他用颤抖的手捡起路上的石头使劲地扔向湖面,然后背过身去,良久,转过身来大声说:“去吧,我决不后悔。”
这世界什么都缺,就不缺女人!”他吐了口唾沫火气十足地说着。
慧敏含泪跑了,湖面上洒下乳白色的月光。解放抬起头来,望着冷冷的残月,揪心地长啸着:“啊——”
却在这时,母亲又染上重病。
他归心似箭,在惆怅的秋雨中踏进他的家门。
炕上坐着邻居的姑娘玉花,见解放回来了,玉花脸上的愁云舒展了许多,说:“大婶整日高烧、咳嗽,我过来陪陪。
你回来就好了。”
妈——妈—”解放伏在躺着的母亲脸前,抓住她滚烫的手,轻轻地喊着,“妈,我是解放。”
母亲听见解放的声音,慢慢地睁开眼睛,期盼地望着他,用另一只手抓着胸脯微弱地说:“疼……”
“走吧,”解放毫不犹豫地对玉花说,“请帮帮我,去镇医院。”
可有好长一段路,又下这么大的雨。”玉花担心地说。
“管不了那么多。”说着给母亲穿好衣服,背着就走出门。
玉花给背上的母亲撑着雨伞。
远处的善代镇,笼罩在白茫茫的雨雾中。泥泞的小路坑洼不平。解放吃力地背着母亲。雨淋在散乱的头发上,渐渐地母亲的身体沉重起来,突然,又遇到一个洼处,他的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路面的浅水里。可母亲还稳稳地在他的背上。解放在玉花的扶助下,慢慢地站起来,可鞋子掉了,赤脚踏着泥水,发出“叭哒一叭哒—”沉重的声音。
“玉花,给我擦擦眼睛,看不见了。”解放说。玉花轻轻地用手帕擦去解放眼里、脸上的泥水,露出仍是清瘦的红红的脸庞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他望着玉花那圆圆的脸蛋、腼腆的眼睛,一股暖融融的感觉涌上心头,小声说:“玉花,谢谢你了。”玉花没答话,只是望着解放一笑。
云层变得暗起来,起伏不平的路面变得朦胧难辨。解放喘着粗气,跑起来。脚下不知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使他跪倒了,玉花吃力地扶起他,可他膝盖上的裤子破了鲜血殷殷地印出来......
母亲在医护人员的抢救下脱离了危险期。可就在守护母亲的第二天,解放忽然也发起高烧来。
“解放,你这是急性肺炎,需要好药,可你母亲的医药费还欠着,大夫说。
“别给我治疗了,过几天会好的。你们可要好好给我母亲用药。”解放恳切地说。
渐渐地解放昏迷了。他躺在病床上不知嘟嘟囔囔地说些什么。消毒后的专用衣服开始严严实实地裹着他的身子,厚厚的白色口罩捂着他大半个惨白的脸,只露出深陷的眼睛,紧紧闭着。他浑身颤抖,发热时仿佛跳进火坑,发冷时好像钻进冰窑,头痛得像要爆炸,肺部呼噜呼噜地响着,又变成急促不安的呼吸声。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只觉得眼前晃晃悠悠,金花乱舞。他沿着陌生而崎岖的山间小路,不停地向前奔跑;身后一群从未见过面的怪兽,张着红色巨口,向他逼近......
“我不想死!”解放突然大喊一声,身子抽动了一下,汗珠从前额、脸颊涔涔地渗出来。他慢慢地睁开眼睛,仍惊恐地望着周围,模模糊糊看见面前站着的是身穿白大褂的大夫,流着眼泪的母亲,红着眼圈的玉花,还有那些微笑着的朋友。
阎王老子没要你,病情正在好转。”大夫从口罩后面传出轻松的声音。
“唉——”解放长长地叹了一声,禁不住泪如雨下,对着母亲像孩童时那样无所顾忌地哭起来……
在分配工作期间,校方说他祖上有政治问题,被审查出了。很快,解放辍学的消息像瘟疫一样传遍全村,人人都说他:“别人念书越念越远,解放念书念回家了,没出息。”
解放突然像掉进一个巨大的黑洞。恐惧与孤独袭击着他,他再也不敢见人了,直挺挺地仰面躺在自家的炕上,整日望着毫无生气的屋顶。屋顶的椽子被蛀虫蛀着,不时地飘下尘土和木头碎屑,落在他的身上、脸上。支撑屋顶的横梁,被熏成漆黑,上面贴着一条横幅,由原来的红色变成灰黄,模模糊糊地辨认出来,写着“抬头见禧”四个大字。
抬头见禧?”解放思忖着。过去,他从未在意这句话觉得那不过是安慰人的话而已。现在他觉得这也许是父亲留给他的启示。抬起头来,就真能看见快乐的事吗?对了,他又想起班主任常老师在他离开校门时,对他说:“解放,你还年轻,脚下有的是路。”是啊,范解放,还得拾起头来,寻找出路。
想到这儿,解放硬是一骨碌爬起来,理理蓬乱的长发。
对母亲说:“妈,我想再找姑妈。
干啥?”
进城当工人!”
三
宏福化工厂。冬天拉原料,硬梆梆的旧皮鞋卡破了脚后跟,疼得钻心,只好一跛一跛地走着。好心的同事要帮他可他笑了笑说:“少一只脚,还能金鸡独立。”夏天检修机器时,不小心头碰在螺钉上,鲜血从蓬乱的头发中流出来,可他只包扎一下,不以为然地说:“割了头,才碗大个疤。
那一天,车间主任郝明堂要他写个《岗位管理法》,他坐在车间办公室,伏在桌上,不停地写。阳光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透过门缝小心地照着他全是油污的脸,他仍低头写着;太阳从头顶的天窗上射进来,照着他沾满灰尘的长发,他还是不停地写着;太阳落下去,电灯亮了,他啃了口干馒头,喝了口白开水,憔悴的脸上露出笑容。他把写好的《岗位管理法》递给郝主任。
主任用吃惊的眼光望着他,说:“这小子的书还没白念。
“不瞒您说,这是我的专长。”解放似乎有些得意地说。
春节刚过,经郝主任介绍,他和玉花成了亲。
解放宴请完朋友和同事,有些醉意,迎着早春的寒风踏着洁白的春雪,晃晃悠悠地往家走。他虽然还是那么精瘦,可胡子刮了,脸上白净而光滑,脖子上的红色领带虽系得歪歪斜斜,可毕竟第一次系上领带。一身灰色的西装穿在身上,显得肥大而不贴身,可被熨斗熨得平平展展,有棱有角。皮鞋擦得铮亮,踏着路上的积雪,发出“喳、喳、喳”清脆而快捷的声音。看得出来,他是个有老婆的人。
门开了,新婚妻玉花那美丽和喜盈盈的圆脸出现在解放的眼前。她正坐在床上铺开被子羞涩地等着他呢。
解放笑着,抱起玉花的腰,“吱溜”一下钻进热乎乎的被窝中。
他那火辣辣的身子,紧紧地压着暖暖的柔柔的玉花,第一次在女人的脸颊、嘴唇、胸脯狂吻着。他仿佛在云雾中探索,在无边的海洋里畅游。他忘记了自己肉身的存在,有的只是长久压抑的欲火痛痛快快地燃烧,淋漓尽致地发泄。他把小巧细嫩的玉花紧紧地搂住,在硬板床上自由地滚动,甜甜地呻吟......
初冬的傍晚,临街小饭馆里传出吆五喝六的声音。桌上杯盘狼藉,盘里早已露出光光的盘底,可解放他们仍不停在碰杯、喊叫。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铁饭碗,变成下岗工人。此时他们正在借酒消愁。
解放对面的张二子,突然抱着头“呜…呜……”地哭起来。旁边的李三指着张二子“嘿嘿嘿”地笑着,说:“你哭…啥……尿……水……多……”说着自己软软地瘫倒,趴在桌腿下打起鼾来。解放左边的王五站起来指着服务员大声嚷嚷:“你,没酒了…怕……爷…不给……你钱是不是……拿酒去……”说着,身子向前一倒,一个趔趄坐在地上“哇”地吐起来。解放右边的赵真,脸色惨白,仰着头,两眼长久地瞪着饭店的吸顶灯不说话。解放指着赵真咬字不清地说:“你……看……啥那灯上……有啥?哈哈……有……有…"说着,又端起酒杯,对赵真说:“赵真哥……咱……再喝后半夜,解放迈着“之”形步子,独自徘徊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
刺骨的寒风吹起马路上的尘土,扑打着解放消瘦的脸和红红的眼睛,他觉得浑身血液奔腾,冲向脑门,兴奋和情不自禁的情绪催着他,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毫无目的地奔跑在空旷、冷清的大街上。他朝远处闪烁着的霓虹灯吐了口唾沫,说:“呸,神气你妈的!”然后在街心“溲—溲地尿起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路边的电灯杆前,双手抱着冰冷的水泥灯杆,大声喊:“郝主任,郝主任,你不管我了?主任,我有母亲,有老婆、孩子呀……郝主任,你说话呀,郝主任。”灯杆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似乎很难回答他的问话。只有上面的电线,发出“吱—一吱”使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声,似乎催他赶快回家,要不就会冻僵。可解放仍久久地抱着沉默不语的水泥灯杆嘶哑地喊着:“郝主任…我有……母亲…老婆……孩子……郝主任……
他的脾气变坏了。那一天,他狠狠地打着要买雪糕的儿子。儿子坐在地上眼泪汪汪地望着他说:“爸爸,我不买雪糕了,你别打我!爸爸,我不买雪糕了,你别打我……爸爸。”他一阵心酸,把儿子抱起来,说:“儿呀,是爸不好,连根雪糕都给你买不起。”说着两颗大大的泪珠掉在儿子的手上。每当妻子捡回半袋煤渣,黑黑的脸庞对他笑的时候,心里总有股难以压抑的内疚折磨着他。
这也许是人性的弱点。解放在此刻,首先想到的是给儿子买根雪糕,给老婆买件衣裳,然后填饱自己的肚子,别的什么都没去仔细想想。
趁午休时间,解放偷偷钻进一个满是泥泞的小巷。他擦了擦满脸汗水,正要拐进一个胡同,突然背后响起摩托声,他回头一看,一位穿着制服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正向他追来。他把自行车一扭,想拐出胡同,向前飞跑;不料,前面也驶来一辆摩托车,向他靠近。糟了,解放想着,急中生智,把身上的小包往矮墙那边一扔,索性停下自行车,站在街心喊:“卖鱼啦,买鱼啦——”。
“站住!”
“干啥?”解放故作镇静地回答。
“你叫范解放?
“本人正是。”
“卖违禁物品犯法,你知道不?”
“我这是卖鱼,谁说我卖违禁品?”解放说着指了指捆在自行车后依架的铁皮箱,里边真的有几条鱼。
“我们接到举报,早已盯上你。”一位工商人员说。
“搜吧,要能从我身上搜出违禁品,你就盯对了;要是搜不出,可别耽搁我卖鱼。”解放辩解着。
“范解放,你老实点,我早看见你把包扔在这里。”另一位穿制服的人员从矮墙后面走出来,提着解放的小包大声说。
“你栽赃,诬陷!”解放硬着头皮死不承认。
罚款5000元,没收自行车、赃物。”一位穿制服的人员伸手要搜解放的衣服。解放推着他们,大声喊:“跟爷动手!”同时伸出拳头冷不防打在一位穿制服的人员的脸上。
混蛋,还打人!”那位穿制服的人员也扑在解放的身上厮打起来。另一位穿制服的人员在旁边用手机嘀咕了一阵。不一会儿,一辆警车开过来,跳下几位警察,给他戴上冰凉的手铐,拉进阴冷的拘留所……
【作者简介】潘瑜,笔名,默林。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原内蒙古骏马化工公司总工程师。工作之余,创作了许多微、短、中篇小说,其中《偏远的善河村》,获内蒙古文联“草原文学奖”,《枸杞红了》获内蒙古文学创作最高奖“索龙嘎”奖,并列为“草原精品小说”,改编为电影《李子王的浪漫事》获2014年呼和浩特市”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山丹之恋》获2019年呼和浩特市”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