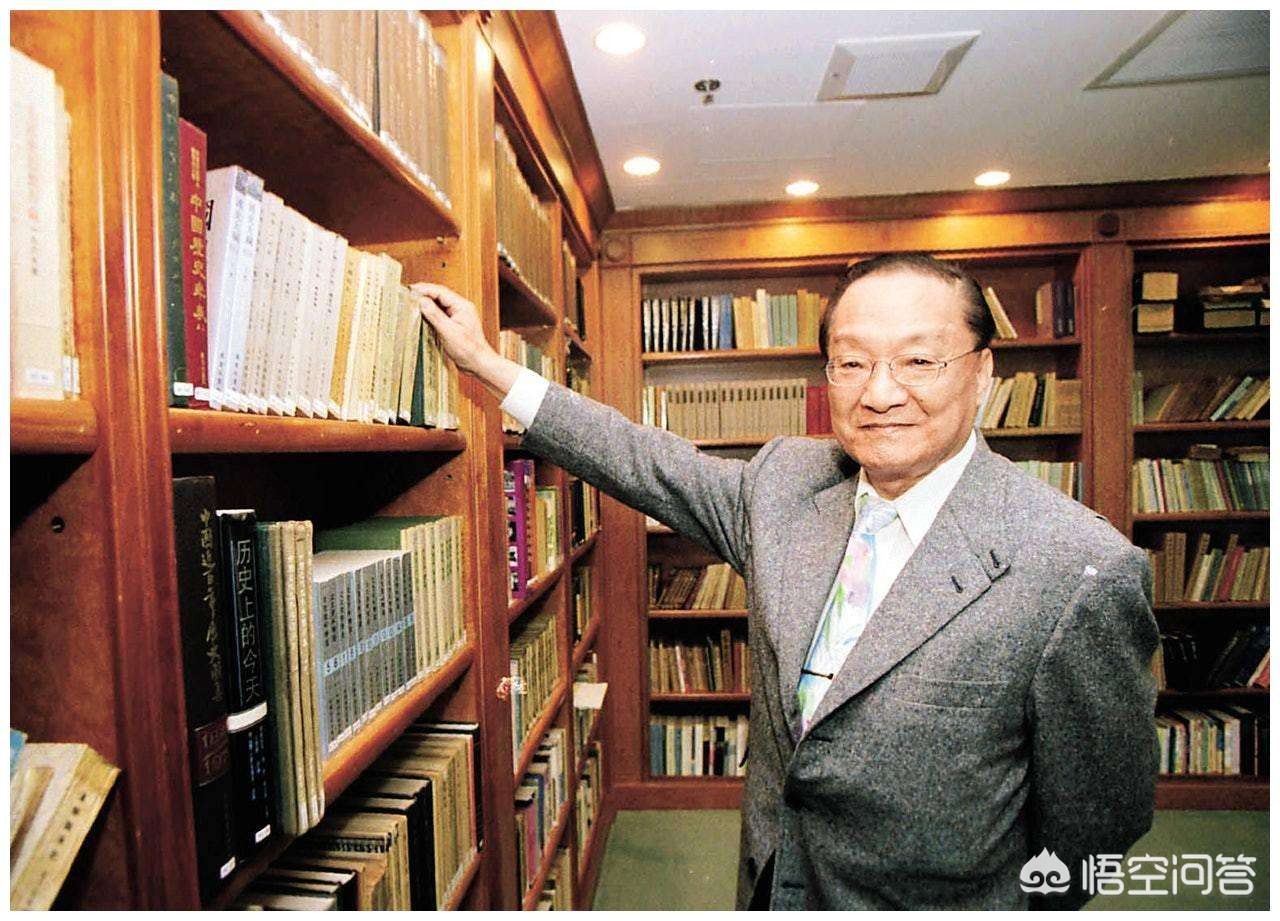人物画与顾陀的“形神兼备”理论
- 时尚
- 2023-03-16
- 106
顾恺之(约公元346―407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属江苏省)人[1],出身贵族,是东晋最伟大的画家。他一生作画颇多,但遗憾的是其作品并无真迹流传于今,只有几幅珍贵的摹本保存下来,即《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传・仁智图》,但是,仅观这几幅精美作品所呈现出的总体风貌,与前代绘画相比较,便从内容到风格、技法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不同和超越,体现出特定时代的新特征。而作为中国早期的绘画理论家,顾恺之强调在绘画中融入士人的人格情操和审美风貌,并在中国绘画理论史上率先提出了“传神论”,将“神”“形”并重、“形神兼备”的思想引入画论之中影响极为深远,并最终使其超越绘画领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传统美学命题之一。
顾恺之现存画论著作主要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观此三篇保存较为完整的画论文章,其中所论又各有侧重:《论画》一篇所论偏重对于摹拓之法要点的阐述,《魏晋胜流画赞》以赏评画作为主,而在《画云台山记》中顾恺之集中阐释了其对于山水画作构思的认知。此外,顾恺之的画论言论还散见于《世说新语》、《历代名画记》、《太平御览》中载录的某些片断之中,其影响同代及后世的传神理论和诸多美学命题就集中于这些画论之作中,其中以形神论影响最著。
人物画与顾恺之的“形神兼备”理论
顾恺之的作画以肖像画为佳,他流传今日的画作摹本也以人物肖像画最为著名,而他自己对于肖像画的创作也最为看重,他在《论画》一文中开篇即言:“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2]他先以绘画技巧本身为人物、山水、狗马等可传递神韵的类题材确立难易程度,从而将人物画置于较优地位。其后又对“台榭”一类所谓器物加以比较品评,“以否定语式,造成其负面确定性,从而形成绘画有限集合的极致边界”[3]。顾恺之以为台榭楼阁一类静态之物,其难处在于技法、笔法的细致入微,就像西方之素描,用力颇多,以精细为佳,难成,但是一旦画成便是佳作,这就是他所谓的“难成而易好”,这一类画作不需通过引起所谓画外之联想便可以得到审美之妙,即“不待迁想妙得也”,顾恺之认为,对于这一类画作不能因为它们是摹形之作就将其视为品级差等的画作,这也是顾恺之并非“重神轻形”的一个例证。
然而,沿着这个思路推进,顾恺之对于人物、山水、狗马一类题材的绘画所强调的就重在“神”似了。也就是说,如人物画构成的要素,除应具有视觉、知觉上的形近之外,还应被赋予一种超乎视觉之外的神似,这就是笔者上面提到的将士人的人格情操、审美风韵通过画作表现出来,这样的画作才是能使人产生“迁想”最终得其妙处的精品。而事实上,顾恺之对于绘画的品评也恰恰在于此。在这里“难成而易好”是与“迁想妙得”相对应的一个价值命题。摹形复杂而难成器物之作一旦绘成便是“好”的画作,他的要点在于构图精细、笔法入微,这类画作定是上品的画作,但是只要用力是极“易”“好”的,实则并不难。而人物画若想要其妙处,所必需的条件是通过为画面形象赋予神韵从而唤起联想,将对于图画本身的关照迁移至画图之外的深层文化维度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人物画作之妙。所以说,对于绘画作品“形”是其外在基础,“形”象则画“好”,但是如果想要达到妙处则必使其具备内部的张力,即“传神”方才可取,这也就是顾恺之的所谓“形神兼备”。
顾恺之在随后的作品品评中便落实了他的这种形神兼备、以形写神的理论,他说:“《小列女》: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又插置大夫,支体不以自然。然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且尊卑贵贱之形,觉然易了,难可远过之也。”[2]顾恺之首先强调了小列女“如恨”的面部特征,指出“仪容”之下“生气”的神的决定性,重在强调“仪容”与“生气”的关系。随后插置“大夫”,以性别的差异配以“支体”的不自然从构图上给出一种视觉判断,而后转锋评其“服章”“众物”之奇,女子之丽形成对比,从而越过画面表象的视感而进入到对于内在气质的判断,而这种源于画面、超出视界之外的文化价值判断才是评价这幅画作优劣的关键所在,即所谓得“神”之妙,然而这些是不可能脱离“形”而独立存在的,强化了其形神理论的涵纳功力。
此后,顾恺之多次强调所谓“骨法”(形)与“神”的结合、处置对于画面的影响:“《伏羲神农》:虽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属冥芒,居然有得一之想”,“《列士》:有骨俱,然蔺生恨意列,不似英贤之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惑以众论”等等。
但是,应当明确在绘画上强调“重神”说并非无源之水,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也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的。《荀子・天论》便云:“形具而神生”指出了“神”是从“形”产生出来的;《淮南子・原道训》也言“形闭中距,则神由无入矣”,说的就是,一旦脱离了“形”,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神”了;东晋嵇康在《养生论》中则说:“君子知形待神以立,神须形以存……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而顾恺之的传神论比较直接的是源于葛洪的影响。葛洪既是门阀士族人物,又是极好神仙道养法、兼修儒道的人物。他的《抱朴子・内篇・明本》有“道者德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一说,而《内篇・至理》则以“形须神而立”,“形者,神之宅”论形神关系。葛洪与顾恺之前辈族人渊源颇深,顾恺之的世界观与葛洪相似者亦不少,且又是道教信仰者,其传神论受到葛洪影响并不奇怪。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内篇・至理》中,对于“形”、“神”的关系问题做了如下论述:“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一作形)劳则神散……”,在这里,他将“形”与“神”的关系比作“堤”与“水”、“烛”与“火”的关系,这些思想为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做了准备,加之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玄学思想风行之时,玄学对有无关系等的探讨,使当时的画家在对形神关系的理解上,获得了一种新的思维。此间佛学又在中国兴起并极成升温趋势,佛学更加强调精神的内容,此两大主流学说的“重神轻形”思潮相融合,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也影响到了绘画创作和人们的审美情趣,同时也启发了画家在艺术实践中对形神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所以说,顾恺之“传神论”的提出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与其所处时代之玄学思想及美学思潮吻合一致的。 二、顾恺之绘画理论对山水画兴起的重要意义
我国在六朝以前主要还是以人物为主的绘画形式,山水常处于人物的背景、铺垫的辅助地位,但是从整个中国的绘画史来看,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画的重要代表之一,顾恺之的绘画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山水画作为独立画科的形成和发展,关于这一点,从《女史箴图》中的山水部分就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独立的山水画之萌芽面目。而顾恺之在这方面的成就,还主要体现在他的绘画理论中,从其《画云台山记》一文中便可窥见端倪。实际上,《画云台山记》本身已经可以被看作是一篇创作山水画之前构图的设计样稿。其言:“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於东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4]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幅山水画的谋篇、布局:山与倒影的结合,云的方位,天空与水的关系等等,这已经是山水画的基础工序,并且完全符合山水写意的意境,而后具体讲每个细节的处理,山“别详其■近,发迹东基,转上未半,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枚,夹冈乘其间而上,使势蜿如■龙,因抱■直顿而上。下作积冈,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复一■,是石。东邻向者,峙峭■。西连西向之丹崖,下据绝■。画丹崖临涧上,当使赫■隆崇,画险绝之势”[4],至此山的部分完成,上下、东西布局勾连,细致入微,正是一幅典型的山峦叠嶂的工笔山水画,已现出山水画家的眼力、功力。此后方才插入人物――“天师坐其上,合所坐石及■。宜■中桃傍生石间。画天师■形而神气■,据■指桃,回面谓弟子。弟子中有二人临下到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答问,而超升神爽精诣,俯盼桃树。又别作王、赵趋,一人隐西壁倾■,馀见衣裾;一人全见室中,使轻妙泠然。”[4]其后“中段”、“西北二面”亦是先置山水,极尽细致,可见顾恺之此时已将山水置于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位置上独立优先考虑了。
当然顾恺之的山水画未必是纯粹为表现山水而作的,但是他确在客观上推进了山水画的成长,可以说顾恺之正是促使山水画在摹实写景的基础之上,向具有独立地位和独立意境方向发展的一位代表画家,在我国传统山水画的独立历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也正是由于顾恺之的画中已具备了独立的山水画萌芽,从而使他成为了我国山水画创始时期的卓越代表之一。
顾恺之的绘画理论对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他将“传神写物”、“迁想妙得”的美学思想与绘画的基本技法(如线条的运用等等)相结合,将我国的绘画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