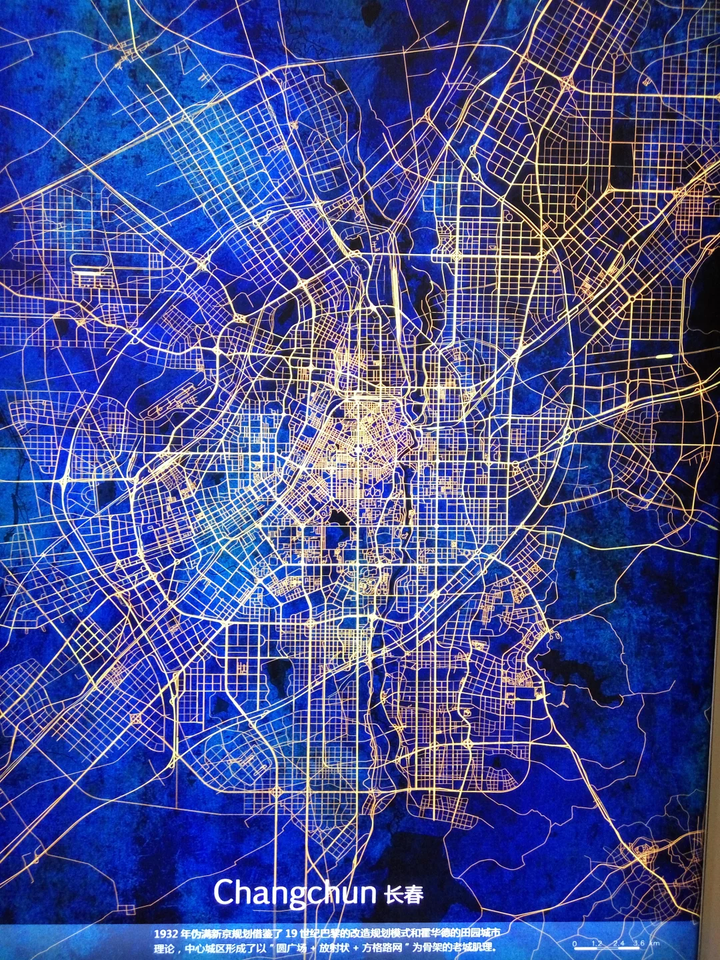马鸣谦:杜甫、马勒与“第九交响曲”
- 综合
- 2023-03-25
- 107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辞严武幕。四月末,携家离成都,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八月至云安,因病滞留。
大历元年(766年)暮春,自云安来到夔州。
客居夔州将近两年,健康状况堪忧,又要为生计辛劳,杜甫却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前后两个秋天,他在创作上都很高产,几乎一天一首的频度。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登舟出峡,先至江陵,过后漂泊湖湘。
大历五年(770年)冬,在由潭州往岳州的舟船上病逝。
时间切换到1906、1907年,奥地利人、作曲家马勒遭遇了命运的三连击:女儿玛利亚去世,在维也纳歌剧院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遭遇了排挤和挫折,以及被医生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古斯塔夫·马勒 (Gustav Mahler,1860-1911),出生于波希米亚卡里什特,毕业于维也纳音乐学院,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
1908年马勒返回欧洲,卖掉了沃尔特湖迈尔尼格的乡村别墅,在南蒂罗尔州的托布拉赫买了一幢农舍静居,重新投入了创作。在这里,马勒先完成了《大地之歌》,过后整个夏天投入了《第九交响曲》的创作。他感到了“命运威胁的迫近”,进入一种 “完全燃烧的状态”。
三年后的1911年5月18日,马勒去世。翌年6月26日,《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次公演。
本文出处:《征旅》,作者:马鸣谦,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
杜甫与马勒:
“生活的痛苦中的欢乐”
初看上去,杜甫和马勒似乎很难搭上关系。两人年代相隔久远,又各在东西两域。不过,马勒在托布拉赫的创作却受到了东方中国的唐诗的直接影响。
据钱仁康教授和其他学者考证,《大地之歌》的灵感来源是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的德语译诗集《中国之笛》(以唐诗的德文、法文和英文译本为参考进行意译)。马勒挑选了七首唐诗的译文,以此为歌词素材,创作出了这部交响套曲。
《大地之歌》包括六个乐章:
第一乐章《愁世的饮酒歌》(Das Trinklied vom Jammer der Erde),歌词转译自李白的《悲歌行》;
第二乐章《寒秋孤影》(Der Einsame im Herbst),歌词转译自钱起的《效古秋夜长》;
第三乐章《青春》(Von der Jugend),歌词转译自李白的诗篇《宴陶家亭子》,德语译名《陶瓷亭》(Der Pavillon aus Porzelian);
第四乐章《美女》(Von der Schonheit),歌词转译自李白的《采莲曲》;
第五乐章《春天里的醉汉》(Der Trunkene im Fruhling),转译自李白《春日醉起言志》;
第六乐章《告别》(Der Abschied),歌词转译自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止》和王维的《送别》。
最后一首歌的标题即《告别》,歌词意境就来自王维那首诗: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也承续了《大地之歌》第六乐章的主题动机:令人心醉的惜别,死亡与忧虑,甜蜜的销魂,无名的兴奋。两首作品都有一个共同基调:对人生和所热爱的世界的惜别之情。在《第九交响曲》最初三个乐章的乐谱上,马勒写有这样一些文字:
“像一个葬礼的过程”
“啊青春!丢失!噢爱情!消失!”
“告别!告别!”
马勒的研究者阿尔班·贝尔格曾如此评论《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第一乐章是马勒所写的音乐中最美丽的音乐。它所表现的是在死亡到来之前对这个世界的深沉的爱,渴望在平静环境中的这个世界的生活,以及对大自然最大程度的爱。由于死亡的必然到来,整个乐章是建立在对死亡的预示上。死亡不断地重复出现。所有对尘世的迷恋达到了一个高峰。所以我们总是在最为纤细的段落后,不停地听到上升的爆发。这种预示最强烈地表现在意义深远的死亡强有力地宣布它的到来的可怕时刻,这是一种生活的痛苦中的欢乐。
“生活的痛苦中的欢乐”,马勒的创作情态与一千多年前夔州时的杜甫是多么相像啊!
杜甫同样也是衰弱多病,同样饱受世间社会的轮番打击,他的幼子和幼孙女同样也先后早夭,更重要的是,他和马勒同样在人生的尾段奋力向上,写出了不朽的杰作。倘若抛开音乐作品与诗歌作品在形式与材料上的差异,仔细鉴赏和比对他们各自晚期作品的基调,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相同处:比如悲愁而壮美的音色,比如命运的浩叹,比如身心的焦灼,比如对尘世万物的眷恋,以及对人类的无私的爱……
这“命运的对位法”,在大脑皮层中生成了闪电,让我在投入《征旅》的前期构思时联想到了马勒。多么及时的馈赠!投入创作的这一年,我反复聆听《第九交响曲》,愈加强化了这个跨界的直觉。
与马勒之前的交响曲不同,《第九交响曲》出现了新变化。之前他往往很强调主题动机的前后贯穿与呼应。而在《第九交响曲》中,这一手法出现了变异,只在最后乐章里有一处引用了第三乐章的“环绕、旋转式的动机”。他以慢板(lento)的第一乐章替代了快板的第一乐章,与已经成为马勒曲风定式的结束部分的柔板(Adagio)前后呼应,形成了在一头一尾的两个慢板乐章中镶嵌两个较为活跃乐章的全新套式。
在乐章之间的调性布局上,马勒之前在《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中让结束乐章的调性比第一乐章的调性移高了一个半音,用以表现肯定的内涵情绪。而在《第九交响曲》中,结束乐章的调性比第一乐章的调性低了一个半音。这是从瓦格纳那里学来的表现痛苦感情的衬托法。
调性布局图式如下(我自作主张添上了一条曲线轨迹):
以上写到马勒的部分,大多引录自中央音乐学院李秀军教授的专著《生与死的交响曲:马勒的音乐世界》,书里有具体作品的曲式分析,令我大开眼界,获得不少启发。
《生与死的交响曲》,作者:李秀军,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8月
杜甫的诗之日记
马勒的作曲法让我想到《征旅》也可以尝试类似的篇章布局,即这部小说可以采用拟近《第九交响曲》四部乐章的结构。《征旅》是我计划中的“诗人传”三部曲的第一部。回想起来,酝酿已有多年:在2015年再次细读陈贻焮先生的三卷本《杜甫评传》后,就生发了初念。2018年,取得了陈先生家人的正式授权,打算以《杜甫评传》为底本编纂一部《杜甫诗大成》,同时开始进入了《征旅》的创作准备。
从《杜甫评传》入手,过后又搜集、阅读了不少和杜甫有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对于《征旅》创作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简锦松先生的《杜甫诗与现地学》《唐诗现地研究》《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日本学者古川末喜的《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以及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杜氏札记》和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诗歌讲演录》。《征旅》的构思是在中日两国杜甫学者共同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它的诞生首先应该归功于这些前辈学者。我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了很多启发,眼目得以打开,同时也感受到他们对杜甫和杜甫诗的深爱的感情。没有感情,是没有继承发扬的动力的。在此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我创作上的恩人,《征旅》的恩人。
《杜甫评传》,作者:陈贻焮,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4月
以小说形式来表现杜甫,不宜完全按线性时间来铺排他整个的人生(那是传记的功用,而不是小说)。小说的作用是聚焦和放大、变奏和强化,因此就需要选择一个能够折映、体现杜甫整个创作生涯的关键时段或典型时段。
与当时和后代很多诗人不同,杜甫是积极表现日常生活的一个诗人,这是细读杜甫诗后获得的一个突出印象。在八世纪的中叶,从永泰元年(766年)到大历三年(768年),杜甫在夔州停留接近两年(加上云安,差不多是三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几乎一天一首!古往今来,从未有诗人如此密集地记录日常生活与抒写精神世界,如同诗的日记或私小说,其中很多内容都可以转化为小说的材料。这是杜甫意欲超越有限肉身的惊人一跃,也是文学史上的不朽奇迹。
另外,杜甫在峡中的三年,尤其是在夔州的两年,在诗创作中展开了大量回忆。因此,聚焦夔州这个时段,向前可以追述他在青春时代、旅食长安的十年和蜀中岁月的片段,向后也可以带出他出峡后的尾声。无疑,夔州时段是小说叙事上最佳的黄金分割点。
结构和调性上拟近《第九交响曲》的四部乐章,叙事内容上以夔州诗为主要材料。做出以上两个判断后,《征旅》就有了一个原型胚芽或初轮廓。
去年(2020年)初春二月,完成《奥登诗选》和《战地行纪》的再版校订后,即以《杜甫评传》和《杜甫诗与现地学》的附录二“杜甫夔州诗编年简目”开始准备创作资料集。由此就确定了“入峽”“火与雪”“农事”“出峡”这四个乐章。如《第九交响曲》一样,“火与雪”、“农事”就是两个较活跃度乐章(与杜甫的实际生活活动非常吻合)。第四乐章“出峡”与“入峽”就是慢板乐章,第四乐章的尾部,杜甫一家重新回到了舟中,再次面对了前途未知的浩茫天地。与“入峽”有着呼应对位的关系。
虽然杜甫夔州诗里的内容已足够丰富,但仍然不足以构成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叙事世界。海明威在谈论小说叙事技术时曾用过一个冰山的譬喻:“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套用一下他的说法,杜甫的夔州诗只是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冰山,剩下的八分之七就需要由叙事者来完成建构。由此就带来两个方向的思考:
第一个思考,是如何经由叙事,使主人公杜甫获得一个全息影像。多年来,我们对杜甫的认知一直停留在诸如“爱国爱民”“忧愤老苍”这类刻板的标签,事实上,这仅是他的某个侧面,而绝非他的全貌。杜甫评论自己的创作时也用了“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这两组词语来表达,表明了他创作上的多样性。
杜甫的性格以及实际生活活动,无疑有着更多的层面和色彩。
第一乐章“入峡”中,杜甫相对比较郁闷、闭塞,社交活动很少。到第二乐章“火与雪”,全家迁入了夔州城中的赤甲宅,杜甫的社交生活也开始增多。他在夔州当地的官员人际网络中是游刃有余的,能够很好地应付处理。而为谋得出峡旅资,后面更是展开了积极活动。他把握时机,最终也达到了预期目标,获得了东屯督田的授权。他关心朝政国事、关心民瘼疾苦,也常为自己仕途的挫折而感怀激烈,自然有“沉郁顿挫”的一面,但这时“随时敏捷”的另一面也表现了出来,能做出务实的判断,也能果断行动。
到第三乐章“农事”,杜甫展开了经营性的行为,其间发生了不少戏剧性事件。“随时敏捷”以外,又展现了了一种类似堂吉诃德的喜剧性色彩。
杜甫的性格中有一种痴魔、狂诞、天真。
痴魔体现在他全身心投入写作时,每当专心吟诗时,他就会完全与外部隔离,不管不顾地投入。
他自少年时起就恃才傲物,狂诞的言行就是此一心态的外化。在成都草堂时,他写过一首《狂夫》,这首诗的后两联就是一幅自画像。即便身处窘困境地,他的志气仍旧那么豪放: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他还有天真甚至不乏可爱的一面,尤其是喝醉酒过后。这方面的事例也有很多,比如他在大历二年写的《醉为马坠,群公携酒相看》和《夜归》。
杜甫爱哭也爱笑,这哭与笑的两面,在杜甫的夔州诗里都有体现。
我后来在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杜甫小传》中的第六节看到了类似的表述,虽然吉川先生讨论的是杜甫喜好谈论政治的一面:
所到之处,对各种事物,立刻就对这对那感到不满,这种性格,作为凭着自己的力量,开拓新的文学真实的诗人来说,至为合适,杜甫诗歌的伟大,也正由此而生。但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却是不适合的性格。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历史就是这样评论的。世间的人们,即使承认他这个理想家中的唐·吉诃德性,也决不会认为他是个政治家。这一点,到了晚年,他自己似亦有觉察。但是,杜甫依然不断地呼号着,表白着。甚至丢人现眼亦在所不辞地不断倾诉着。
元 佚名《杜甫像》
第二个方向的思考,就是如何在《征旅》中模拟交响曲中的多声部效果。除了杜甫这个主要声部,还需要其他声部来配合、对比和协调,如此,这个叙事世界才是有机的,丰富的,可信的。
简略而言,这个多声部来自于他的家庭生活和外部社会生活。因此,除了杜甫以外,就需要围绕他建构起一内一外的两组群像。
家庭生活构成了内部的群像,由家人妻子杨氏、长子宗文、次子宗武、二女杜堇,僚奴阿段和婢女阿稽、信行、柏夷、辛秀。
上述人物中,四个少男少女(宗文、宗武、阿段和阿稽)构成了一个可以抵消成人严峻生活的缓冲部,一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突破族群差异的小社会,一个小乌托邦。从少年们的视角,可以折射杜甫身上那种类似唐·吉诃德的“狂夫”色彩。
与夔州使府官员、过境官员和各色居民的社交活动构成了外部群像,这其中有夔州历任主政者、使府官员、将军、当地小吏、屯田行官、僧人、商人、伎乐人等等,也有夔州本地住民、农人和船工。有些出自杜甫夔州诗中的真实记录,有些就需要做合理的推想和虚构。
在众多走过场的人物中,无疑夔州刺史柏茂琳是一个焦点。
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杜甫诗应该以何种面目出现在小说中。我不想让《征旅》降格为杜甫诗的串讲,让小说变成诗的附庸。因此,结合上述关于小说布局结构的思考,就做出了如下的处置:在小说正文中不出现单篇的诗作,尽量将诗作内容消解、溶化在叙述语流中,杜甫的吟句可以变作他内心独白的一种。出现的诗作要有利于塑成整部小说的基调。
《征旅》除了第一乐章“入峡”部分有穿插性的回忆段落,基本上还是采用了常规的线性时间叙事。不过,在线性时间叙事中也叠合、糅入了不同人物、不同视角的平行叙事,即以杜甫的主观视角为主,根据情况再同步穿插多种视角。这次,我还努力学习(不是照搬)了萨拉马戈在《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中的技法:将客观白描、主观独白、上帝视角与多人物视角相互交叉,随时可以作无缝跳接。巧合的是,萨翁这部小说也是以诗人为人物原型(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
先要能够看到、感觉到、触摸到,然后才能写出。这是我的一个写作信念。当我深深沉浸在杜甫诗篇的氛围世界中,原先横亘在面前的古人与今人、过去与现在、偶像和读者、诗与生活之间那些障碍壁垒已不复存在,杜甫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标签、一个被偶像化的大诗人,他变成了我可以感知、可以接触、可以了解的一个同时代人。当思虑的意念足够集中,沉浸的时间足够长,我的惊喜发现就越来越多,到最后,那个闪光的时刻就自动到来了:我能清楚明白地看到杜甫,看到他周边的各色人物,看到夔州的一切。原先纷乱的线索被开始变得有序,过后各自聚合又相互生成。当捕捉到开篇第一句话的语调后,《征旅》就自动展开了。
自(2021年)6月中旬动笔,到10月31日写出了初稿。12月2日,《征旅》诞生。第一乐章“入峡”的叙述时间点是在永泰二年(766年)。这间隔了一千两百五十五年的回望与致敬,现在已告完成。
作者/马鸣谦
编辑/张进 李阳
校对/陈荻雁
本文为马鸣谦杜甫传记小说《征旅》之代后跋,经作者授权刊发,有略微改动,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