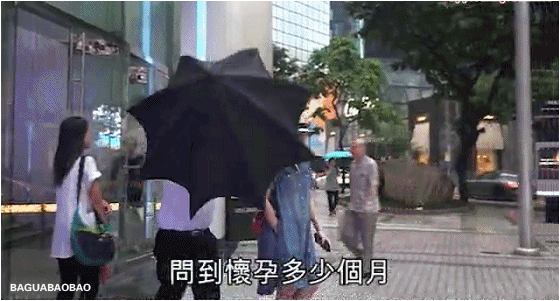从数字资本主义视角,剖析数字劳动分工 | 社会科学报 马克思
- 财经
- 2023-04-19
- 68
从数字资本主义视角,剖析数字劳动分工 | 社会科学报
马克思主义研究
● 数字劳动分工的本质是数字劳动者之间的数字社会场境内聚力。在数字交互中发挥作用的是总算力,具有海量数据的算法机器人替代了只能一行一行编码的单一数字个体。
● 数字劳动分工是数字劳动自身的非总体化过程,当数字生产数像化构序的完整数字劳动被拆分成环节性单一质性的数据时,数字劳动者原本完整的数字劳动力和创造力才能被完全地剥夺。
原文 :《从数字资本主义视角剖析数字劳动分工》
作者 |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温旭
图片 |网络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通过劳动分工揭示了工人共同活动中产生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反向对象化。然而,在数字时代来临之际,这一切又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历史认识论的视域中,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无疑为我们从数字劳动过程层面深化了数字社会场境关系存在论,扩展了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视角。在数字劳动之前,人类已经经历了两类分工。第一类分工是由亚当·斯密发现的,在手工业生产阶段,社会劳动拆分为不同的劳动部分,并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简称为“社会内部的分工”。第二类分工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在工厂生产阶段,单一商品的生产被拆分成不同部分,简称为“工厂内部的分工”。
到了数字时代,在前两类分工的基础上,出现了 数字劳动分工,是同一个数字劳动被拆分成多个数字子劳动,由“前端—中端—后端”的数字劳动者们分担,简称为“劳动内部的分工”。处于数字劳动分工中的每一位数字劳动者的数字子劳动都仅是这一数字劳动过程的一个片段,只有在数字劳动过程的最后才形成数据商品生产的数字劳动总体。
从简单协作转变为智能交互
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在数字时代以不同质性的数字交互场境出现。数字劳动已经完全突破了原本物与物的连接和生命负熵过程,借助数字劳动者有目的地把本质之相构序于对象的数像化创建过程,使得数字活劳动时间变成数据的全新持存模式。没有数字劳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无法实现数字生产中数字劳动者借助代码构序数字程序的数字劳动数像化过程。
数字劳动者们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不论是数字劳动技能,还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程序的使用,都在数字劳动者之间生成了紧密的相互连接场境。数字平台是数字劳动交互的同一个数字社会数像化空间条件。数字平台生产中的数字劳动交互是“前端—中端—后端”众多数字劳动者的协同数字子劳动。前端数字子劳动主要由用户型数字劳动者完成,例如Facebook用户、Amazon用户等;中端数字子劳动主要由零工型数字劳动者完成,例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后端数字子劳动主要由专业型数字劳动者完成,例如算法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等。
数字劳动者之间的数字交互,必须以一个数字社会数像化的数字定在为前提,即是同一个数字空间中的数字劳动交互,这就是数字社会数像化空间中数字平台的出现,其特点在于对数字程序和大型服务器的共享,以及数字劳动者之间的数据交互、相互促成数字子劳动目标的实现。
数字劳动分工的本质是数字劳动者之间的数字社会场境内聚力。在数字交互中发挥作用的是总算力,具有海量数据的算法机器人替代了只能一行一行编码的单一数字个体。数字交互中的数字劳动者的内聚力,已经异质于工业劳动中的简单合力,这是可以发挥出数字个体“剩余数据”(surplus data)的场境关系赋型力量,这当然也是生成性数字劳动时间质性的要素。
数字劳动交互创造了数字社会生产力。这是数字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交互性总体数字社会力量,由此,这种通过数字劳动交互生成的数字社会力量不隶属于数字个体的数字劳动力,其并非自然力,而似乎是独立于数字个体劳动的算力。
从数字劳动对象化转变为数字平台生产
数字平台的出现呈现出由主体数字劳动向客观数字生产的决定性转变,这就是数字剩余价值的基本逻辑点, 数字平台生产中的数字劳动过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数字平台生产的规则是将数字生产过程拆分成各个功能环节,并应用数字技术来加以解决其中发生的问题。这个规则起到了决定性影响。由此,数字平台掌控了数字生产的全过程。数字劳动者借助数字平台通过有目的的数字劳动数像化行为构序数据的主体性数字劳动过程,这一构序数据的活的数字劳动时间,逐步转变成数字技术构序数据的数字子劳动。
数字平台生产并不进行数字劳动。也就是说,数字平台生产过程的数字劳动的主体在场性是否定的。从本质而言,数字主体支配的“剩余数据”演化为客观自为的数字劳动体系的彻底断裂。数字技术的本质是有目的的数字劳动数像化构序数字程序,之后反向对象化为数字生产方式。
同一个数字生产技能借助数字技术的数字程序化,在完全脱离数字劳动的情况下,产生单纯数字技术数像化构序,且反向对象化数字生产为数字平台。其目的并非简单重塑数字行为,而是不断生产数字平台内部的直接对象化数字技术的数像化构序数据的客观连接。
这代表着原本工业生产中工人有目的生产的劳动物相化过程,在数字平台生产中发生根本性断裂:一方面,数字生产目的已经不再是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潜能,而是远隔数字劳动者的数字技术研发和算法黑箱的操控结果;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并非开放源代码给数字劳动者可编辑的反向对象化,而是数字技术构序的对象化。
这导致原本以数据为中介的主体性数字劳动过程,转变成数字技术数像化的数字平台生产过程,而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构序的在场性直接消散,转化为数字平台生产过程的操控者。
从数字交互转变为数字资本操控
数字劳动分工是数字交互深入发展的形式,也是数字资本在数字生产过程中提升数字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式。
数字交互是完成同一数字工作的多位数字劳动者的交互行为,是单个数字劳动者有目标的自发主体活动的连接场境。然而,数字劳动分工则不一样,其已并非数字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连接场境,而直接呈现出数字劳动者之外的客观性数字生产规则,这一构序并非来源于数字劳动者,而来源于组织数字生产的数字资本。
与数字交互中的数字劳动者进行完整的数字劳动行为不同,数字劳动分工则把完整的数字劳动分割成多个数字子劳动,再通过数字技术从数字生产过程的整体上把其构式成完整的数字劳动生产。这也是数字资本借以提升数字劳动生产率并获取相对数字剩余价值的手段。
数字劳动分工是在数据交互中发展而来的数字社会劳动的分化,前后接续且不同的数字子劳动发生分离并分担不同的功能。在数字社会总体上,这些数字子劳动是片面的,并不能直接生产数字生活资料,而只有借助把自身的数字子劳动与其他子劳动相连接才能获取数字生活资料。
这些数字子劳动生成的数据呈现出特殊的数字劳动类型,单一类型的数字劳动者唯有借助数字连接而发生数字交互,才能把“剩余数据”转化成数据商品,进而占有数字社会生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这是数据商品生产和数字交互可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数字劳动分工之下的“汇聚、连接”,并非数字个体完整的数字劳动数像化构序数据的主体性连接,而是碎片式数字子劳动之间的非主体性聚合。作为数字劳动数像化的自觉的“共同活动”已消失,原因在于数字劳动分工中的共同活动并非数字劳动者的共同连接在场,而是由外在的他性总体性促成的。
对数字劳动者而言,数字劳动分工是将执行每一个特殊环节的数字子劳动数像化为冰冷的纯粹代码,归结为某种简单的质,这种质从表面上看是丰富多彩的数据产品,但其实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相同数字行为,数字劳动者的所有数字生产力和数字技能都为了这一“质”而被剥夺。
数字劳动分工已是数字劳动自身的非总体化过程,当数字生产数像化构序的完整数字劳动被拆分成环节性单一质性的数据时,数字劳动者原本完整的数字劳动力和创造力才能被完全地剥夺。数字平台生产进程中数字劳动者之间主体性交互中的数字社会聚合力消逝于客观算法系统中。算法对数字劳动分工与交互聚合力的吞噬,恰好是以数字技术应用中的数字主体编码为条件的。数字劳动不再直接变成数字生产生成数据的推动力,已经并非“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算法的编码者,而是数字生产的数字子劳动环节——数字平台智能运作的参与者。一旦脱离这种数字异化的“整体机制”,数字劳动者就变成了一行字节跳动的代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3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拓展阅读
情感劳动,或将改变社会生产方式 | 社会科学报
视域 | 数字排毒:一场数字行动主义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