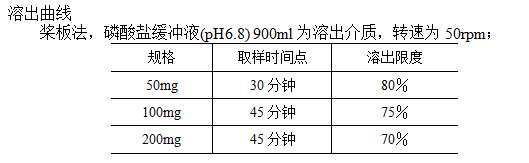刘奕谈陶渊明的真诚与自由
- 文化
- 2023-05-09
- 82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奕多年来潜心于陶渊明研究,近日,其论著《诚与真——陶渊明考论》的新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就陶渊明的生平、作品、精神世界、文学风貌中“重要而又文献足征”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刘奕认为该书与其说是他的陶渊明研究,毋宁视为他对陶渊明的理解,而“诚之以求真”就是他对陶渊明人生哲学及实践的概括。在接受《上海书评》的专访中,他说:“我认为陶渊明所思所行始终围绕如何安顿身心,如何获得自由展开。我想知道的是,他究竟是如何从思想资源中汲取所需,如何去实践,最后才能安顿身心,在作品中呈现出一个既笃实诚悫,又真率潇洒的形象。”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刘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538页,108.00元
先从书名说起吧,这本《陶渊明考论》的主书名“诚与真”来自特里林的《诚与真》,在那本书里讨论到了关于作者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情感与实际情感之间是否一致的问题,而在您对陶渊明的考论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觉得他其人其文都是“诚且真”的?
刘奕: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这本书的名字应该叫“诚之以求真”。我很喜欢特里林的《诚与真》,喜欢他在保守与自由之间博通圆融的手眼,于是借用这个书名,有向特里林“致敬”的意思。在特里林那里,诚是真诚,真是真实,他认为二者在西方语境中其实是贯穿现代性“自我”的基本问题。在十六十七世纪,社会性自我最初被认识到之后,人们希望保持外在的社会自我与内在的精神自我的统一,这种内外统一就是真诚。到了十八世纪,这种内外统一产生了冲突与分裂,精神自我开始渴望突破社会的束缚。于是一种新的卢梭式的真诚观出现,它要忠于的是那个不变的精神自我。但这个不变的灵魂式的自我却有惺惺作态的嫌疑。于是到了十九世纪,文学家开始在生命和生活的真实状态中去发掘一个真实的自我,去揭示出包裹生命的种种虚饰,以此完成文化上的自我重塑。这个重塑的自我既是觉醒的精神自我,也是内在与外在、真实与真诚重新统一的自我。而二十世纪的思想与文学,因为批判社会对自我的结构性压迫,倾向否定自我统一的可能性,否定文化上、道德上塑造自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潜藏在特里林的文字之下的似乎是这样一种焦虑:如果现代性的自我是在个体与社会分裂、摩擦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抛弃社会,回到一个底层的、疯狂的、彻底孤立孤独的非社会自我,是不是意味着自我的重新“湮灭”?这是我所理解的特里林《诚与真》的思想主线。
陶渊明的诚与真显然不是特里林所描述的现代性现象,但我们在回应当代学者对陶渊明的种种新思考之时,又不得不时时反思我们所持的各种现代立场。就像特里林所概括描述的,西方人对真诚与真实的理解一直在发生变化,我们是否可以从变化的观念河流里任意舀一勺水作为衡量古人的镜鉴,这是大可反思的。理解陶渊明,首先还是要回到陶渊明所生活的历史世界中才好。在一个玄学盛行的时代,陶渊明观念中的“真”不可避免地受到玄学的影响,他心目中理想的人生境界应是顺从本性,自生自化,进而齐一大化的生存状态。有意思之处在于,陶渊明并不像一般魏晋名士那样,在纵乐中“忘我”,或者仅仅满足于思辨与清谈的快感,他整个的人生态度相当笃实诚悫。无论看其诗文表达,还是考察他的生平行迹,都会发现他对德性、对善抱有极大的信心,他努力使自己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并认为这样的生活符合自己的本性,是通往真之境界的切实途径。我于是借用《中庸》中“诚”和“诚之”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德性上的自觉自反。在这个意义上讲陶渊明诚且真,不仅仅是说他无伪,更是在描述他所具有的心性自觉。一个人有心性自觉不等于他再无过错,再无一点虚饰,他只是能反躬自省,过而能改。能反躬自省便是诚之,过而能改,坦然面对便是真。由此而实现的光明澄澈、无妄求、无忧惧,甚至忘我的境界,则是更大的诚与真。
在书中,您反对田晓菲在《尘几录》中关于宋人“发明”了陶渊明的说法,也谈到了对于陶渊明人格和境界的推崇是从他身后就开始的,那么在您看来,陶渊明是否存在被后世理想化或者一定程度地“被塑造”的问题呢?
刘奕:田晓菲教授敏锐地看到宋人对陶渊明存在理想化解读的情况,问题在于是否能得出宋人“发明”陶渊明的结论。要知道,脸谱化、标签化,是我们认知他人的基本方式。对不熟悉的人、单纯听闻的人,我们往往是根据其身份、地位、成就、年龄、籍贯或自我标榜、社会认同等而得到最初的认识。除非变成熟人,否则我们的认识一般也就停留于此,而不会变得深入立体。脸谱化认知不但不可避免,而且人的天性倾向于神化著名人物,会对已有的脸谱化认知添油加醋。越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离我们遥远的人物,越是无法逃避这种神化。记得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说过:“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几乎狂热。”文学家早已洞悉的人性,文学研究者可不能忘了。陶渊明生前已名列“寻阳三隐”,同时人自然是按照隐士的形象来看待他、想象他。死后厕身《隐逸传》中,后人更要按照隐者的标准来解释他、传说他、崇拜他。总之,被脸谱化、标签化是我们每个人活着时就无法避免的事,死后就更不用讲了。其实,越是平凡的人,越容易被人刻板认知,因为他们往往被忽视。反倒是伟大的人物,他们一方面会被持续神化,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因为被后人全方位打量,反复研究,不断书写,而获得摆脱扁平化宿命的机会,最终拥有一个立体的形象留存于历史记忆中。
陶渊明看来有幸进入了伟大者之列,所以宋人一边按照历史记载,强调他是一个高尚的隐者,一个忠义之士,一边希望更充分而全面地理解他。比如苏轼对陶渊明决绝洒脱人格的强调,对其作品绮丽丰腴特性的发现,比如黄庭坚将陶渊明视为不得志的诸葛亮,再如宋人开始细致考证陶渊明的生平,编写了好几种年谱。单个看,也许会以为某人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塑造陶渊明,合起来看就会发现,正是宋人开启了立体化理解陶渊明的进程。事实上,正是宋人开始广泛地为古今人编撰年谱,这显示了宋人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意识,以及他们希望立体理解人物的意图。当然,理解者都有自己的视域,有自己的前理解,洞见与偏见相伴而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如何,这些属于理解,而非无中生有的创造。这与霍布斯鲍姆他们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所揭示的编造历史、创制传统的“发明”,性质和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陶渊明“守拙归园田”、拒斥“尘网”的形象是为我们所熟知的,而您在书中阐述了他其实是同时与污浊人世和冷寂山林(包括宗教)保持距离的,“世间名利场”与“世外白云乡”他都不愿托身其中,他是怎么保持人生取向上的这种平衡的?
刘奕:“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这是我们都熟知的陶渊明的自述。陶渊明的归隐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他要归入的不是与世隔绝的冷寂的山林,而是人境中温暖的田园。我想,这一选择首先跟他的性格有关。他倔强兀傲,与俗世两相厌、两相弃。同时他又有勃勃的生命力和深醇的情感。他自述“良辰入奇怀”,有奇怀的人,生命力旺盛,不可能枯寂于寂寞之滨。而后世不少学者,比如梁启超,还注意到陶渊明是个“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是个极看重亲情与友情的人。所以他要留在独属于自己的一片田园中,这里同时与热闹和枯寂保持足够的距离,又能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与生活的温度。其次,也跟他的内在需求有关。我在陶渊明诗文中看到他表现了三个层次的心理需求:疏离、接受和安顿。疏离是对俗世之恶的拒绝和远离。“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这样的表达与姿态,在陶诗中并不罕见。接受是对世界的接受,是认识到美丑善恶交织才是世界的本相,就像《饮酒》诗中所说“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而安顿则是“结庐在人境”,在心理与现实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以安放身心。在逻辑上,疏离和接受是安顿的前提,在现实中则是三者交织并存。陶渊明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知,有随时反躬自省的能力,因此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会堕入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境地。实际上,为官作宦也好,修仙拜佛也好,都意味着接受更为主流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意味着被更主流的人群接受和认可。而陶渊明选择的路则是尽量摆脱社会认同,回到较纯粹的自我认同。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生存方式,是我们多数人在青春时代会萌生,而很快又被现实碾得粉碎的理想。古人常常标榜的“名教中自有乐地”,以及“中隐”这类,其实都是理想向现实妥协的饰辞而已。陶渊明没有妥协,同时他又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理想需要现实的支撑,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所以他选择躬耕的方式,让人生切切实实安顿在自己的手中。后来顾炎武也是四处垦田耕种,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然后才能践行他“行己有耻”的人生格言。他们都是以躬耕为有所为,然后才能坚持自我,有所不为。
对于历代争讼不休的陶渊明是儒、是道还是儒道融合的问题,您认为玄学与儒学都对他产生过深切影响,而他的关注点始终在生命的安顿上,是通过儒家的道德意志来实践追求庄子真的境界、自由的境界,他是如何“消解了自由与道德的矛盾”达到这种自洽的呢?这种会通儒道的方式是不是不仅在魏晋、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特殊性?
刘奕:是的,宋代开始,人们喜欢辩论这个问题。看下来,主张陶渊明是儒家的学者似乎略占上风。但陈寅恪先生以“新自然说”概括陶渊明的思想,并以为渊源在道家和道教,也有极大的影响力。说句题外话,梁启超以为陶渊明一生得力和用力处都在儒家,但又认为他根本没有耻事二姓、忠于晋室的念头。陈寅恪视陶渊明为道家思想人物,同时又反对梁氏之说,而力主陶渊明就是晋之忠臣。没有忠君观念的儒家,拳拳忠爱的道家,两相对照,非常有趣。两位先生在分析陶渊明的思想时,都还遵循着现代学术的规范,可是一旦进入忠不忠的问题,便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投射了太多自己的影子到陶渊明身上。虽然洞见与偏见总是相伴而生,但研究者还是需要多做自我反省、自我反诘吧。
回到陶渊明,他没有留下专门的说理文章,也不见他有注释过思想经典的记载,读完其作品,我们会承认他有思想的兴趣,但很难说是思想家。非要给他贴标签的话,恐怕生活家、文学家更合适吧。对这样的人物,是从他整个的人生出发来审视他的思想兴趣与实践,还是先判分他的思想,再来分析解读他的人生,哪种方法更好呢?我倾向于前者。我认为陶渊明所思所行始终围绕如何安顿身心,如何获得自由展开。让自己的生命削足适履,臣服于一家一派之说,把自己变成儒家或者道家的信徒,这种情况我们无法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得到验证。我想知道的是,他究竟是如何从思想资源中汲取所需,如何去实践,最后才能安顿身心,在作品中呈现出一个既笃实诚悫,又真率潇洒的形象。我目前的结论,即您说的他是用儒者内省不息敦行实践的工夫来追求庄子所描述的“真”的、自然的境界,或者说是凭借道德意志以希企心灵的自由。道德与自由是否矛盾,不同思想家是有不同回答的。老子、庄子会觉得矛盾,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孔子不会,主张名教与自然合的玄学家也不会。不过孔子的自由是德性自我完全实现的境界,玄学家郭象的自由则是“性分”的充分展开。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这是庄子和玄学影响下才会产生的认知,但他又说“结发念善事”,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表现了很强的德性意志。对他来说,一生的工夫,都是要摆脱“心为形役”的困境,即借由德性的自我砥砺来摆脱身体对心灵的劳役束缚。可以进一步认为,他承认身体和欲望对心灵的自由来说是最大的挑战,需要依靠道德的约束,才能真正“复得返自然”。这个思路显然与郭象拥有共同的出发点,却最后分道扬镳。这种认知,在我看来,更接近于宋代士大夫的心性之学。虽然看不出陶渊明是孟子意义上的性善论者,他也更加不会以天理来规定“性”,但他修身养性,而归于心灵自由的主张和实践,又的确颇与宋人相似。宋人论性,是要复其性。陶渊明“归去来”“归园田居”,关键也是一个“归”字。他所归的,表面是田园,实际是自然之性,所以仍是归其性。一者归,一者复,所归复者都是本性,所以陶渊明能在宋代得到那么多崇拜者,绝非偶然。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很早就谈到过陶渊明对于生死问题的焦虑,而您在书中也提到王国璎先生认为史传有意回避了陶渊明焦灼的一面,那您是否认为陶渊明存在这种焦虑?如果是的话,这又是不是最后他能够通达“纵浪大化”的前提?而史传和后世的评述中是否确实有有意回避的倾向呢?
刘奕:陶渊明自然有焦虑。生死、贫贱、善恶有无报应的问题都会困扰他,其实这些都是前面所说的“心为形役”的不同方面的问题。陶渊明其人和其文的可贵,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他能光风霁月、天然真率,以及他写得出自己的胸次,更重要的是他不自恋不自怜,不会自我粉饰,而是坦然写出内心的种种焦虑、挣扎和一次又一次的超越。那么,《宋书》《晋书》《南史》和萧统所写的陶渊明传记是否有意回避了陶渊明的焦虑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不应夸大和苛责。前面提到过,史书中陶渊明传记都在《隐逸传》,即在类传中。类传有类传的体制,我们很难想象一部写焦虑的隐士和隐士的焦虑的《隐逸传》。作史者并非不在意写出传主的个性,但写出个性不等于像现代传记、现代小说一样,要全方位立体地刻画传主。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就说,他作史传,要取法《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后世史家,也都秉此原则。所以对史传写作,还是要有同情之理解,不宜苛责。而且说句公道话,跟其他隐士的传记比较,陶渊明的传记是相对最不类型化的了。因为陶渊明有不少作品传世,作传者摘录这些作品,自然就展现了传主的个性。我们不能光看史家自己的文字,而忽略了他们摘录的原文。比如《宋书·陶潜传》,就引录了《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和《命子》四篇作品。《归去来兮辞》和《与子俨等疏》中都颇有袒露内心的焦虑矛盾,而《命子》诗郑重相告以家族历史,期待儿子光耀门楣,体现出来的不正是陶渊明的不同侧面吗?至于萧统的《陶渊明传》,朱东润先生更是在《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中推许为南朝单篇传记的第一名作,认为完全写出了陶渊明的个性。我很赞同这个判断。知人论世,首先还是要回到古人的历史语境才是。
您谈到陶渊明终其一生都在努力体认和表达一个复杂的自我,并且在包括《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饮酒》组诗、《形影神》三首等代表作中展现了反复确认自我而获得内心澄澈的过程,这个非常有趣,能略展开谈一下吗?另外,您还提到他五十四岁前后在作品中展现了遭遇到最大的自我怀疑危机,这个具体是指什么?
刘奕:可能有些读者会有种刻板印象,以为陶渊明一生都处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里,结果发现他还写了不少表现焦虑、愤怒和困惑的作品,便觉得从前看到的“悠然”出于伪饰,或者觉得陶渊明的境界不过尔尔,这些肯定都是误会。孔子自述“乐以忘忧”,但《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喜怒哀乐之情都有,并不是永远处于喜乐状态之中。又《论语·泰伯篇》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以颜回对,称赞他“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正说明有怒,不贰过也说明要犯过错。再如《论语·泰伯篇》载曾子临殁之言:“《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也是说要死了,今后再也不用担心犯错了。圣贤之人,依然会有喜怒哀乐,会犯错,他们与常人的区别,只是“仁以为己任”,“内省不息”,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而已。陶渊明作品所展现的,也正是这样不断自省自新,超拔向上的一生。比如早年所写《五柳先生传》,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全文频繁出现的“不”字为全篇之关键,其意在破除一切尘俗之见。这就是一次在社会规范的对立面找寻、确立精神自我的尝试。确立自我,才不那么容易被裹挟而动摇。所以他坚持到差不多二十九岁,实在太穷,才出来谋个官职。在后来断续做官的岁月里,他写过几首行役诗,这些诗也反复在描述精神自我与社会自我对立的苦恼,和回归精神自我的志愿。在最后一首行役诗《乙巳岁三月为建军参军使都经钱溪》中,诗人展现了一个被束缚的自我在山川风物中苏醒的过程。他“晨夕看山川”,看到“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一种自由之感油然而生,于是醒悟“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这里描述的“觉醒”非常真实,因为到了这一年十一月,诗人就彻底辞官,永归田园了。身体上回到田园容易,而心灵上回到本性、回到自然自由之境却不那么容易。政局和社会的巨变会强烈刺激心灵,身体的生理的欲望与困扰也并不那么容易摆脱。所以陶渊明一次又一次通过作品袒露内省的过程,并反复确认那个精神自我。其中,大致作于五十三、五十四岁之际的《饮酒》二十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以及《感士不遇赋》,让我注意到他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并不好,充满怨愤与质疑。这些作品反复在与《史记·伯夷列传》作潜在对话,始终在思考善恶的代价这一问题。我们看《饮酒》组诗,其一写荣衰之无定,其二写善恶报应之虚幻,其三写此身之独一可贵,其四写束身归心之艰难,这四首诗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由质疑外在世界而确认内心世界的心理过程。确认一旦完成,著名的《饮酒》其五出现了,诗人再次在重获自我的同时进入自由之境,诗歌中的天地澄澈,万物自得,都是这种自然与自由感的体现。而且比较早年与晚年作品,陶渊明早年所认知的精神自我还比较简单,也就是“性本爱丘山”而已;晚年的自我就复杂多了,他要一次又一次战胜内在的焦虑和矛盾,他要承认这个世界的滋味就是苦涩,然后再来确认和建设自我。他对世界的认识和质疑越深刻复杂,经自省而获得的自我就越深沉厚重。《咏贫士》其一的“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直写出了人生永恒孤独的况味,让人惊心动魄。
我注意到,您谈到后世诗人中,在唐而言,最像陶渊明的是杜甫,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王、孟、韦、柳诸人;而在宋人的人生态度与实践中,最具陶风的也不是追和了一百多首陶诗、以头号崇拜者自居的苏轼,而是黄庭坚。为什么这么说?
刘奕:关于后世学陶诗人的系谱,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不能仅仅或者主要把风格作评判标准。打个比方,父子祖孙之间,有时未必那么像,反而两个相隔万里的人,有时会惊人地“撞脸”。但前者有血缘关系,后者没有。再如鲸外形像鱼,其实是哺乳动物,其DNA测序证明它和河马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我们评判古人的文学系谱也是,风格只是一个提示,还要综合去看其自述,以及比较其字句章法、修辞习惯、诗思诗意、主题话题、文学观念等等,然后才能做出有无“亲缘关系”的判断。这样综合评判的话,杜甫与陶渊明是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的,王孟诸人就不那么肯定了。我举些证据。首先杜甫有不少推崇陶渊明的自述,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的“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还有《可惜》的“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等等。字法上,我在《诚与真》书中举过陶杜二人用“在”字的承继关系。另外好用虚词,二人也相同。句法上,杜甫《示从孙济》开篇“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从噂沓,且复寻诸孙”,显然从陶诗《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来。这一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早已指出。论章法之拗折,也是陶杜一脉相承。而合字句章法,能以文为诗,杜甫之前,便是陶渊明。构思用意上,如杜甫《谒真谛寺禅师》“问法看诗忘,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与陶诗《和刘柴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所居”正同。当然,杜诗中也不乏风格上就像陶诗的作品。比如《夏日李公见访》,清代焦袁熹评为“似陶诗”,杨伦直接说“景真语旷,绝似渊明”。此外,题材、主题的承继性也很明显。杜诗有很多田园作品,清代黄生曾经说:“杜田园诸诗,觉有傲睨陶公之色。其气力沉雄,骨力苍劲处,本色自不可掩耳。”讲到了二人的同与不同。另外,乞食这一主题,陶诗之后,也是杜诗写得多且好。更进一步,二人的诗歌创作都以坦诚真率为特征,温州有位已故的老学者吴鹭山,在《读陶丛札》中就特别强调过杜甫在性格的真率上最像陶渊明。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陶杜二人的诗作为“自传诗”的代表。不过他不大认同“真率”这一判断就是了。把以上各项相似点、承继性综合起来看,杜甫与陶渊明的亲缘关系就要大大超过王孟韦柳,特别是王孟柳。
至于苏轼、黄庭坚谁更近于陶,我是在比较他们的人生观与心性实践的时候提出我的看法的。苏轼天才纵逸,豁达超迈,所见的陶渊明便主要是他真旷的一面,黄庭坚在心性与道德人格的追求上比苏轼更执着,他又得了禅宗的法脉真传,在“诚之以求真”这一点上,黄庭坚的确是很接近陶渊明的。
最后来说说谈及陶渊明总是绕不过去的“见南山”“望南山”之争吧,在您的专著中,这个问题是被归在了“作品六考”里,有非常详细完整的考证,但其实孰是本字是并没有结论的,勾连这个争论比较有意思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见”字最后胜出了,以及陶渊明到底是不是有意为诗、是不是有精心炼字。在考证之外,您能就这两方面略作梳理吗?
刘奕:关于“见南山”和“望南山”的竞争,就像您说的,我的小书中已经说得挺多了。简单讲,考证的结果不支持“见”字出于宋人“发明”的看法,两个字互为异文,至少在唐代就是如此。但究竟哪个是本字,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得出结论。也许就像王叔岷先生猜测的那样,之所以有这两个字,可能是诗人修改的结果。可惜时代太过久远,我们再无证据来一窥究竟了。这时,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只能是何以“见”字会在竞争中获胜,成为多数人认可的“本字”。有些学者认为这完全是苏轼的影响力造成的。苏轼的意见和影响力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苏轼发表过那么多意见,他说陶渊明的诗超过李杜,说王维的画胜于吴道子,批评《文选》去取失当、卑弱,可是人们并没有就此奉为金圭玉臬,作为抑扬去取的标准。可见,苏轼的某个意见能得到广泛认同,一定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文选》的兴衰是个重要原因。“望南山”是《文选》保存的文本,而《文选》是唐代到北宋前期的科举必读书,一般读书人幼而成诵,对“望”字习以为常。但是到了神宗朝科举改革,进士科罢诗赋而改试经义,《文选》风光不再,“望”字也随之变得陌生起来。同时,宋人的审美风尚已渐渐从唐人的华丽热烈转变为淡逸、自然、朴素,陶诗的风格自然容易受人青睐。所以在苏轼之前,推崇陶渊明的宋人已经很不少,《陶渊明集》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而陶渊明集的文本大多是作“见南山”,“见”字于是为大家所熟知。正好从唐代钱起到宋代梅尧臣、沈括、苏轼,不断有一些较敏感的诗人意识到了“见”字可能更有表现力,这种认知与宋人的审美相一致,于是得到广泛赞同。总之,人心与社会复杂多变、交错联络,哪怕微小的现象,也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归因往往并不能带来正确认知。
至于说陶渊明是否有意为诗,是否炼字,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古人常常说陶渊明无意为诗,这是对的。这个无意为诗,是指无意文坛争胜,不会为了迎合时尚、获得名誉而写诗。他写诗有时是单纯的抒慨、自省或自娱,有时是向亲友表明心迹,委婉表达各种拒绝的意思。而具体写作,根据现存的诗歌看,陶渊明的写作态度大都是很认真的。他真率自然与诚恳笃实的风度很妙地交融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使得他的诗洒脱自然又真切笃实。认真写诗的人,当然会考虑如何用字。陶诗用字有时也有曹植“惊风飘白日”、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这种醒目字眼的选择,比如“崩浪聒天响”“中夏贮清阴”这类诗句,但并不太多。一个诗人如果只知道炼这种醒目字眼,就像时时刻刻都在争胜较劲。胜负得失心太重的话,对文学的虔诚就会受损。如果对文学艺术有足够的虔诚与信任,那还有另一种炼字,即追求字词的准确贴切、恰如其分,使人初读似无所见,细品又拍案叫绝。就像杨万里形容陶诗“雕空那有痕,灭迹不须扫”,这个描述太准确了。这种用例,我在小书的各处,曾随文作过揭示,另外第六章中《形容的尺度》这一节还做了专门讨论。这里不妨另外举个例子。《咏贫士》其六:“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寔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最后这个“聊”字就很妙。“聊”是姑且、聊且、暂且的意思,“长相从”就是要一直相从追随,又如何是“暂得”呢?首先,它表达了一点无奈,即“寔由罕所同”,诗人自述跟张仲蔚一样,实在不能合群,只好彼此相从了。其次,“聊”字带有一点调笑,甚至“撒娇”意味,用这个字,表现了诗人在深心里把张仲蔚视为亲近的、可以调笑的朋友。再有,诗歌前面描述张仲蔚“爱穷居”“所乐非穷通”,试把末句改作“正得长相从”“誓言长相从”“深愿长相从”,比“聊得”如何?改了之后,语气便显得斩截亢直。斩截亢直是介,却不是真正放下,那前面所云“安”与“乐”就成了虚言饰辞。唯有轻轻松松、随随便便一个“聊得”,才是真放下了,是真有所安与所乐的口气。这个“聊”字不是后人所谓“诗眼”那种刻意醒目的字眼,却用得恰到好处而力重千钧,有它,诗歌才结得自然而洒脱。我想,读陶诗的秘诀,正需要在这种不起眼的字词上多加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