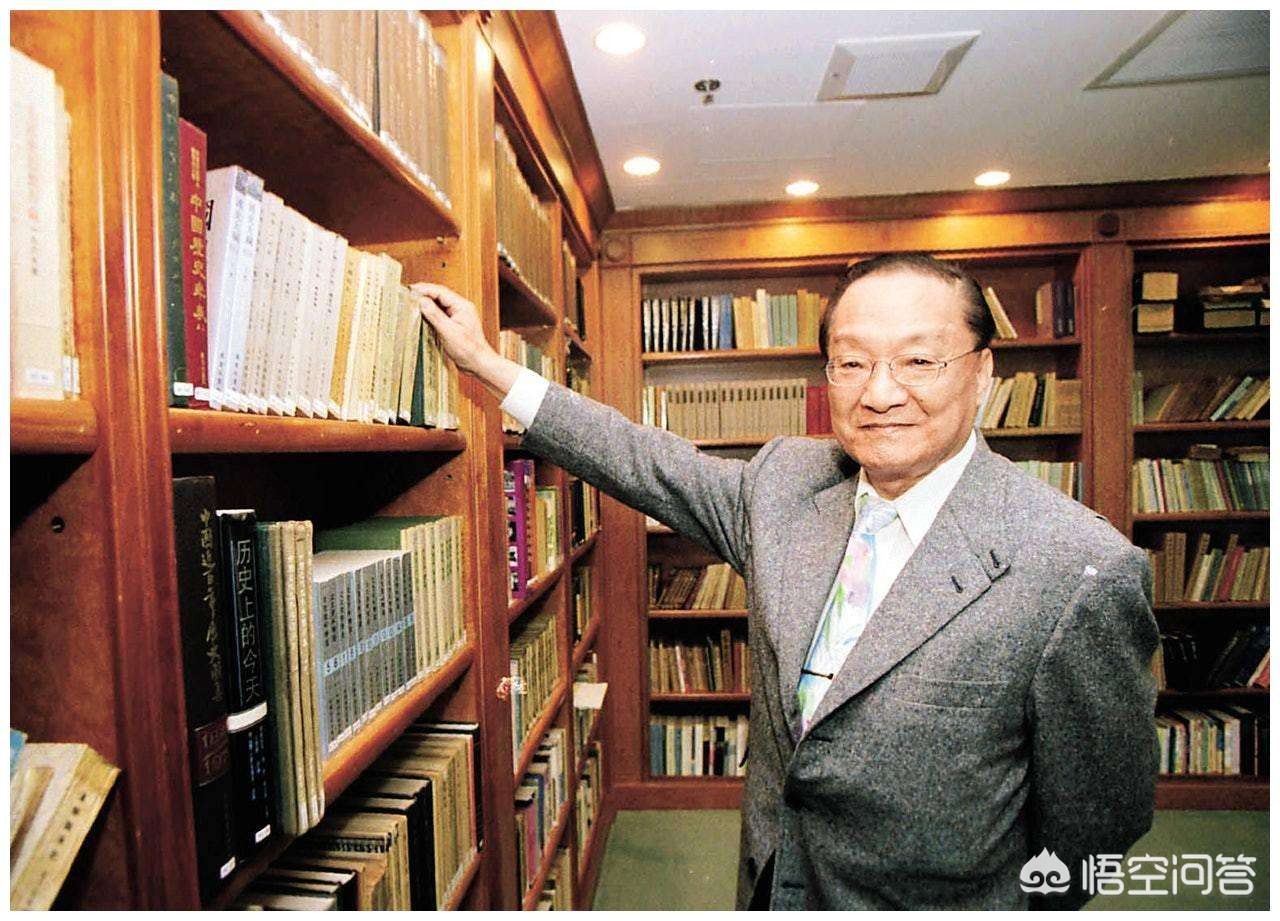当最闷的书店,开始成为网红
- 娱乐
- 2023-05-18
- 97
当最闷的书店,开始成为网红
《书店里的影像诗》剧照。
27年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的中山大学西门外,一家以文化学术图书为主打的书店“学而优”开始与读者见面。
曾经的市场热烈欢迎学而优的诞生,它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鼎盛时期,学而优的分店数量多达30多家。然而,在数字时代的冲击下,实体书店步入了夕阳时期,学而优也不例外。在疫情期间,学而优数次暂停了营业。
前不久,学而优宣布重启。只不过,这次的主理人不再是学而优的创始人陈定方,接手学而优的变成了1200bookshop的主理人刘二囍。这个一直以来被认为格外沉闷的学术书店,凭借一系列打卡属性极强的活动和装潢登上了社交分享平台首页,迎来了一波流量的高峰。
伴随流量而来的是质疑的声音:当书店变得越来越“网红”,书店还能保持纯粹吗?带着这个问题,新周刊记者和刘二囍、陈定方聊了聊。
✎作者 | 许峥✎编辑 | 张文曦
刘二囍说,学而优不再要“严肃的、沉闷的、暮气的”四壁。
他思索着排列出三个形容词,尝试概括这家过去30年里几乎不修边幅的老学术书店,以一种追忆的语气,给它翻了个页。
而后,他挑拣了一句更隐约的表达——“我们从未现代过”——印在收银台上方,七个摘自拉图尔书封的繁体字构成暧昧语感,整个店面打散又重构,频繁地被拍摄、被注意、被推上社交分享平台。
印有书店名与拉图尔肖像的灯箱。摄/林泽君
刘二囍接手得很干脆,也没多少选择:要么选择一件显眼的外衣,否则大概率会被湮没在明明灭灭的报道里。
《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中可以看见,2019年关了500多家,2020年再关1500多家……知名的、不知名的独立书铺一一旋紧门闩,连同贝克特、海德格尔、列夫托尔斯泰的书架一块儿推倒,残骸被登记成数字。
怎么挣钱、怎么吃饭的问题一直存在,自本世纪初至今天,书店一路凝视亏损的深渊,还要一路遭遇着“媚俗与不媚俗”的抉择。
就如同重启的红色按钮,常常在分岔口不由自主地闪烁。
在一众凝视中重启
3月25日,学而优正式移交给新主理人刘二囍,话筒、书脊、字幅、邀请函在灯光中聚成涌动的影子,新港西路93号的客流量迎来了一次少见的爆发。
它细细地吊起纸灯,光线柔和,作家语录与肖像开始浓烈地从四面八方涌现,小说家画像被复印、装裱、高悬到墙壁上,素描般直截的眼神透过玻璃,审视某个地方。
相框中的波德莱尔。摄/林泽君
重复且密集的摘抄像藤蔓一样爬满灯笼纸片,毛笔字从天花板流下来,那些砖瓦、字迹与宣纸笼罩整个铺面,焦距一调,非常上镜。
仅仅一夜,学而优就突然被很多双生疏的眼睛记住了,它拖曳出一个行业内早已蔓延的共识——只卖书无法呼吸,讲情怀显得贫瘠。
为了生意,茑屋、言几又、钟书阁早早就开始对抗孱弱的收支,计算赚与赔,高调地立起玻璃幕墙,镜像中反射的各色论著层层叠叠拾级而上,主理人用几亿人民币投资一个令人晕眩的学识领地。
钟书阁旋转的室内设计。图/图虫创意
去钱锺书隔壁舔一口提拉米苏,循着纳博科夫的名字挑拣香薰,倚在勃朗特身边试戴项链……这些书店像是要反省以前那种毛坯似的破落书店的失败经验,急忙拿时髦的公式来求证,纸张里也许会有商机。
可怜的是,它们照旧躲不过坍塌,拥有一年3000万人次客流量的言几又轰然倒下,从58家门店缩至3家,它们缺钱、欠费、入不敷出,彻底裸露出国内书店摇摇欲坠的骨架。
就这么不被看好地,学而优从废墟中抖了抖身子,借拉图尔的书封说:“我们从未现代过。”
书架上的字幅。摄/林泽君
“我们从未现代过,不是否定当下这种生活,也不是说我们前现代,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我们从未现代过》的译者刘鹏坐在巨大标语下,解释了这句话,“我们应该打破边界”。
《我们从未现代过》
[法]布鲁诺·拉图尔 著, 刘鹏 / 安涅思 译
拜德雅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4
它在市场上再次诱发了这一很少成功却被密密麻麻地求解、追索的难题。
我们从未现代过
1996年,陈定方循着中山大学附近拆除的砖墙要了120平米小地,在知识分子下海与新华书店丛生的市场里,凿开一个可以高频出现“主义”“革命”“近代史”的角落,取名“学而优”。
它储存冷僻的人文社科书籍,谈论“唱片中的性别文化”“民歌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闻真相背后的真相”,邀请小河、林生祥、五条人来低唱,从小小几十坪连绵生长出34家分店。
2010年在学而优举办的某场活动海报。
那是顶旺盛的时期,却也只保留不说废话的书籍,“过去觉得,书店它还是应该要只卖书”,几万种论著满坑满谷,非常合理地占据掉了一切腔调与花样。
“一进来很直观的,满眼全是书,没有别的,那种学术的、知识的、思想的氛围非常浓厚,我会想把整个书架一排一排逛下去,很多书都有阅读门槛,不是随便买回家都读得明白。”
旧书架还保留着。摄/林泽君
一位女性顾客在楼梯前停驻,“它确实不是一个很大众、很普及的书店,几十年来,教授们到这儿都能买到理想的书,就像北京的万圣、上海的季风,它在全国学术书店里很排得上号”。
与此同时,学而优没什么抢眼的物件,“书本身就成了唯一的装饰,都是些社科类、学术类,20多年不曾变过,很少点缀,装修也比较沉稳”,创始人陈定方很熟悉这种二十多年前的气质。
几台旧式铁风扇垂下来,竖柜、横台、壁橱里的书籍满满当当,像个二话不说的仓库,翻页是这个地方唯一会发生的动作。不读书的人顿觉枯燥,读进去的人暗自沸腾。
博尔赫斯书店创始人陈侗用一句话和盘托出了这类学术书店的力量:“就是所卖的书除了带给人阅读快感,再也不附加什么别的感受。”
座椅上的读者。摄/林泽君
媒体习惯用“纯粹”来报道它们的事迹,那是一种长久以来毋庸置疑的印象,且被读者保护着、渴望着。但不可避免地,行内行外都在焦灼地追踪它们当中发生的一次次缓慢陨落。
当“10万册1元书”的直播间提示开始滚动,当复合连锁书店一时间几乎要燎原,舆论当然下意识地反问——
“纯粹”去了哪里?
现实不存在纯粹
“只卖书是救不了书店的”,刘二囍接过这个喧闹已久的问题。
他腾挪原有的书柜,往里填筑文艺标识,灯笼、纸片与楼梯随处切割出漂亮的视觉棱角,仿佛在脑中筹备了一次小规模清算——从淡漠的旧陈设,到月亏损将近10万人民币的财务账本。
二楼的纸片高低错落。摄/林泽君
“书店动不动就活不下去,快死掉了,书店很大只是看起来很赚钱而已”,他坐在漩涡似的讲座小场子旁边,“而且每当我们讨论‘纯粹’时,界定都不清晰,难道只卖书才纯粹吗?”
这个小声说话的空间里,阶梯高处悬挂起庞大的毛笔字帖,低处涌现了对准模特找角度的摄影者,快门声与翻阅声各自为政,二楼落座区散布餐饮单,柔软而宽厚的皮椅子盛惠一杯美式。
这条楼梯成为出镜频率最高的背景。摄/林泽君
“来流量是好事情,到了现在还去讨论为什么真正的读书人不来这里,为什么只剩下网红打卡之类的问题,已经太滥俗了,读者本来就一直在流失的,你知道吗?”刘二囍早就忖度过网红这个话题。
自9年前创办1200 bookshop起,不大好听的窃窃私语始终萦绕在他与他的书店旁,网友纷杂地敲出“一个书店搞得这么刻意”“很怀疑流量会为书买单”“网红连书店也要侵蚀”等句子。
诸如沙发客、24h留灯、一个书店决定去死、保卫独立书店直播等概念与事件,推着他时而浮上赞誉的浪头,时而沉入质疑的水底。
在网络上,“国风”“氛围感”“新中式”是学而优的关键词。/社交分享平台截图
“说我改得花里胡哨、不好好卖书的这种声音很多,但在我看来,书店是一个文化休闲空间,只有空间才不会被电商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取代,如果硬想办法卖书,那有点无路可走。认清现实,放弃幻想。”
刘二囍不避讳这一务实的逻辑,比起“基本不会去营销”的陈定方,比起“觉得点缀不太符合原有调性”的读者,他斩钉截铁地撕裂了大部分人要坚守的严肃感——“因为不破不立”。
学而优书店门口亮起的灯牌。摄/林泽君
“网上说只卖书才是值得尊敬的,OK,是尊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绑架了我,不负责任地、七嘴八舌地。只有作为最近距离的运营者,你才知道那个痛在哪里。”
他见过小书店倒闭的痕迹,主理人欠了一屁股债、家庭支离破碎,就像一团凌乱而难以拆解的线团,“我有代入感的,好好工作、热爱阅读的理想主义者何以至此?”他不希望活在悲情叙事里。
“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跟大家说别把我当文化人,聊书的话跟读者和图书部同事聊去,我就是一个生意人,别觉得算账就是市侩、庸俗,只有脱掉长衫,才可以干这些体力活。”
一串被定格的逝世时间。摄/林泽君
在学术书店弥漫着“夕阳”“悼念”“拮据”等词语的时代里,刘二囍直言自己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但他不要可贵,“很多人都终将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了,凭什么书店就必须全然不变?”
被争议的“言几又们”
穿针引线一般,学识与生意在这个行业有过好几次轰动的缝合。
钟书阁设计出重重镜像,反射出一笔笔丰腴的投资;西西弗垒起500多万会员,刷出冗长的咖啡小票;言几又蘸取了书架、餐厅、市集、沙龙、艺术品等各色脂粉,去雕高高的梁与栋。
“那一度是风头无两的,满屋子玻璃,投资要拉好几千万”,网红的电流在陈定方耳边不断爆破,“到处都在开店的,你看各种请日本的设计师来设计,我的同学也跑去参观,没怎么买书。”
“可是心底里觉得不太对,我接受不了假书,还要堆那么高,你有本事就用真的书去填它好不好?这种我觉得就叫贩卖情怀了。”
言几又书店的楼梯与书架。图/图虫创意
在网红的语境里,书籍就像一个杠杆支点,要么量准了动力臂,要么随时哗啦啦地,旋转楼梯、摺纸天花与学院拱廊悉数倒塌。
“我知道书店是挣不了钱的,你拿投资人的东西得有回报,人家不断地拿着鞭子在后面给你抽,那怎么弄?”陈定方观察着烧钱的浓烟,“最后变得像疯了一样,拿各种各样的东西加进去”。
“小孩找一个书店来打卡,说明他还是对文字有内在的、很隐藏的渴求,是吧?最核心的东西要保留,总不能只剩下个光怪陆离,书店如果用一种直白的商人思路来做,那根本没办法。”
书店人脑中有种种框架与次序,用来安排语言的在场。
墙上挂有伍尔芙的某本书封。摄/林泽君
从3月份至今,刘二囍只搬动学而优的柜位,具体的书籍该艰涩艰涩,“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比如说北京万圣,面朝那些你想看看不懂的书,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像去教堂一样变得低调,而大型字体可以凸显这个色彩”。
比如各地书店那些横亘在梁柱之间加粗的“自由”们,比如单向街挂出的《追忆似水年华》们,那就是一场滞销书的清脆吆喝。
“‘贩卖情怀’当然是个坏词,但坏词有时也是必要的,就像生活中必须有‘坏人’一样”,陈侗没有把它想得过重,“有动作就会有反应,事先都估计得到,谁也不希望无声无息的”。
某天,刘二囍翻找拉图尔的旧海报,那行字确凿地暗示了一个重启的姿势:“我们从未现代过。”在学而优收银、找书、阅读、讲座的各个场景里,它都像个指印般被誊录在白纸中。
夜晚的新港西路93号。摄/林泽君
刘二囍知道重启的铁轨总是要震动的:“被讨论、被争议有时候是件好事情,网红只不过像文青那样被贴上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太多人喜欢带着一种偏见、一种自我的角度去衡量书店”。
“一个书店能够活得不错,这就很牛逼、很厉害了,假如言几又不经历关店潮,我觉得是好事情,但分店消失时很多人是拍手叫好的”,他记得很多远距离崩裂的例子,“书店其实真的很弱”。
一楼大多是人文社科书籍。摄/林泽君
“坦白说,这个社会有一百间书店,跟只有一间书店很不同,当先锋开了很多家店的时候,大家说要是人再少点的话我就更喜欢它了”,他硬邦邦地回嘴,“这话对我们来说不太爱听”。
“此时此刻,我开的就是一个文化休闲空间”,刘二囍不想说场面话,“成为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妈的,太难,你成为好了”。
二楼的阅览区。摄/林泽君
而陈定方也有相悖的难处:“我心里就那么一点点东西,只会开书店,这三年处于一个很停滞的状态,甚至是往下走,不靠别的很难支撑,那么我现在交出去了,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弄。”
“现实中不存在纯粹性,它只存在于理念层面”,刘鹏摁住激光笔,指向投影幕布里的“我们从未现代过”,“大家总是强调割裂,把存在封在不同的空间里,其实联系是很重要的”。
在学而优重启整整一个月之后,老牌书店博尔赫斯搬迁筹款的消息传开来,它的推文结尾是:“打字时,‘筹款’的旁边出现的是‘愁苦’”。
· END ·
作者丨许峥
编辑丨张文曦
校对丨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