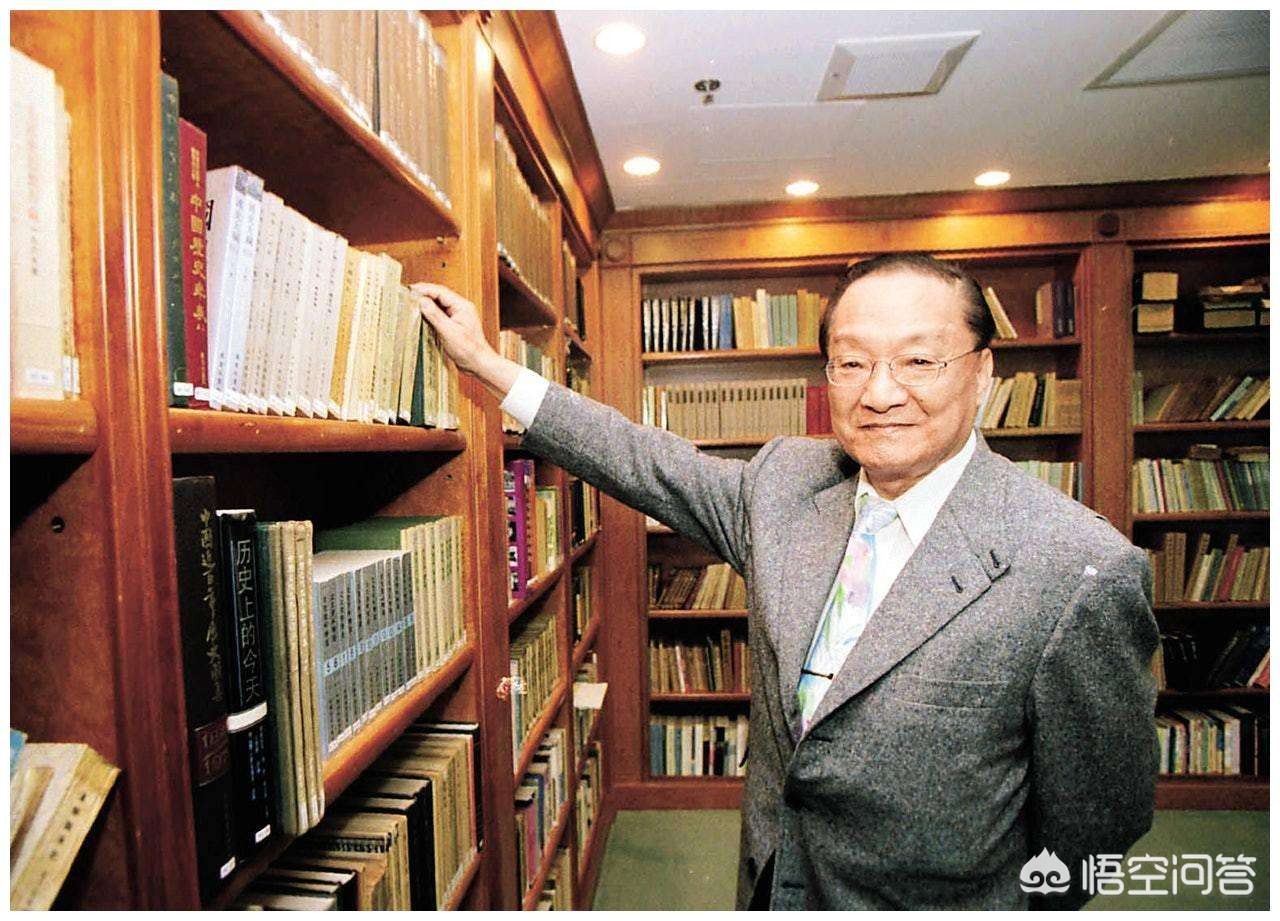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
- 娱乐
- 2023-05-15
- 122
□朱白
在曹寇的小说集《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中,一群少年或中青年,他们叫王奎或者张亮、李芜,等等,他们准确而又僵硬地活在这个世上,既感动不了别人,也在大多时候无法满足自己,他们游走、徘徊、停滞、向上、向前,面带笑容或者偶露狰狞,在他们充满无奈和被动的人生旅途上彳亍而行的表情里,永远带着一股荒诞却又真实的劲儿。
《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曹寇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8月版,58.00元。
那些跟所谓凡庸生活无关的东西,在作家曹寇看来,仿佛越来越不重要。比如一位文学女青年半夜不睡觉一个人深沉而悠然地酗着酒,还比如文人墨客之间那种刻意的手写书信、互道一声某某老师、X师——至少,这些跟我们活生生本应充满血色和无聊的生活没有关系。它们不值一提。
所以,曹寇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知识分子或者跟他本人一样身份的作家、艺术家之类的人物,最多的是那些小人物,小公务员、小教师、小混混、小职员,那些整天在地上摩擦着泥土、浑身都飘逸着某种肉味儿的不足挂齿但也无比真实的人。
小说集在目录那里共分了四辑:“在校期间”“在社会上”“王奎的几种死法”,以及“综述”。我最喜欢的一辑是“王奎的几种死法”。作家用几乎都是平淡的口吻描绘了几种人世间的死法,它们常见或偶见,它们甚至称不上是“法”,因为过于司空见惯或者缺少可供归纳总结的类型。“被打死的”“坠楼而死”“双赴黄泉”“未知死因”,他们的死可以剔除掉时代背景,而存在于人类的任何历史。换言之,曹寇笔下的主人公之死并没有寄托作家本人的虚妄指向,而是刻板地一笔一画地在描述某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困境。我们都无法摆脱死的纠缠,对于活着的人来说皆是如此,不管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或者幸运的还是不幸的,在生之年都挣脱不掉这件事对自己的魂牵梦萦。
面对死亡,作家有意地总是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去处理,也许死本身确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也许只有那些远离死的人才会将之做放大放大再放大来理解。你离它越近,反而会有一种越为平常的心理。死这件事的本质,在小说中好像只是一件轻松平常的事,跟我们傍晚约了朋友喝酒,然后散场,各回各家一样,只是这里的散场是再也不见了的意思。死,也可以娓娓道来,不加任何情感的渲染。
曹寇的小说,时常会有一股明显的挑衅意味。也就是说,你作为读者在亲切阅读这样一部小说集的时候,某个时候可能会感到被冒犯了。
在《春日即景》中,作家将一位罹患重病与病魔纠缠的朋友,与自己的某种情欲,交织在一起写,形成某种反差和互为映射的效果。春天、重病、桃花、手术、逗狗、卧床,它们怪异地出现在同一篇小说中,但又彼此毫不唐突。
“然后我就对小高说了一句话,她听明白后拔腿就跑掉了。”这里的一句话大概是段子之类的玩笑,作者没说,虽然他知道读者读到这里时一定想知道,但他就是没说,这里的挑衅意味已露端倪。后面作者直接提出了一句疑问句——“没追也许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后面我得谈这个问题。”但是后面没有再出现这个问题,这种反悬念的写法已经明显带有“与读者为敌”的意思了。小说的结尾也如此,两个悬念中的男女,终于单独相处,而作家只对景色、阳光、声音做了刻意的描写,努力把读者所谓期待的谜底消化在了无聊的景致之中。
曹寇的“恶意”“敌意”或者称之为恶作剧情节,总是要体现一二。在《晚报新闻》中,他一上来就描写了一位相亲中的女青年因为紧张而不断喝茶,进而上厕所的想象情景。相亲,上厕所,这不是于谦老师的段子,而是小镇青年的一肚子坏水。“并画有一颗雪白的骷髅,照例为两根同样雪白的臂骨交叉托起。每次我看到这个,总想起一句脍炙人口的话:让我们托起明天的太阳。”象征了死亡和极度危险的骷髅图标,被作者不无戏谑地联想到如此反差的一幕,这当然也是一种恶作剧,如同本篇小说中的一句“我真不理解她为什么总是自杀未遂”一样,充满了戏谑和浓浓的恶意。
曹寇笔下的主人公尽管一如既往地流里流气、但也一直把某种“腐朽”挂在脸上,他们其实都很传统,受限于某种庸俗的伦理观和道德观。“他俩分手后,我不可能还跟李芜有单独来往。”这里是指与朋友的前女友来往,是一种不道德的事,当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当然,有时候诸如道德上的某些束缚,就是被拿来冲破和挣脱的。
出现在《鸭镇夜色》中的十六篇短篇小说,是作家多年累积而成,有几篇甚至我好像在十几二十年前就读过(也许是错觉),如今再读,只能再次承认,它们皆是没有争议的当代汉语小说经典。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毫无疑问的程度想必会越加浓烈。
如果说有什么不满足或者困惑的地方,那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作家还在执迷于只写“传奇”?普通人的传奇,虽比超级英雄的传奇接地气,但也会显得狭隘,是少数化、精英化的产物。除了“我”以外的人不是怪死,就是以不得志的蠢货或者其他类型蠢货的面目活着,只有“我”,早晚会得到那些让人夜不能寐的女神,或者过上一种显而易见不那么蠢的日子……每个主人公都太像主人公了,而男二号又只能是男二号。
我们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在书写这种传奇,这跟小说质量无关,也跟个人喜好无关,你能想到的优秀和拙劣的小说几乎都是如此。哪怕是可以冲破束缚限制猛力调侃和自嘲的王朔,他小说的主人公也是这种“传奇”。别人都可以死、可以被动,而“我”只能活着、只能主动占有这个世界,哪怕有一天“我”也不得不或悲壮或缠绵悲痛地死了,那也是一种刻意渲染了情感的死——这种死不再普通,不再庸常如你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