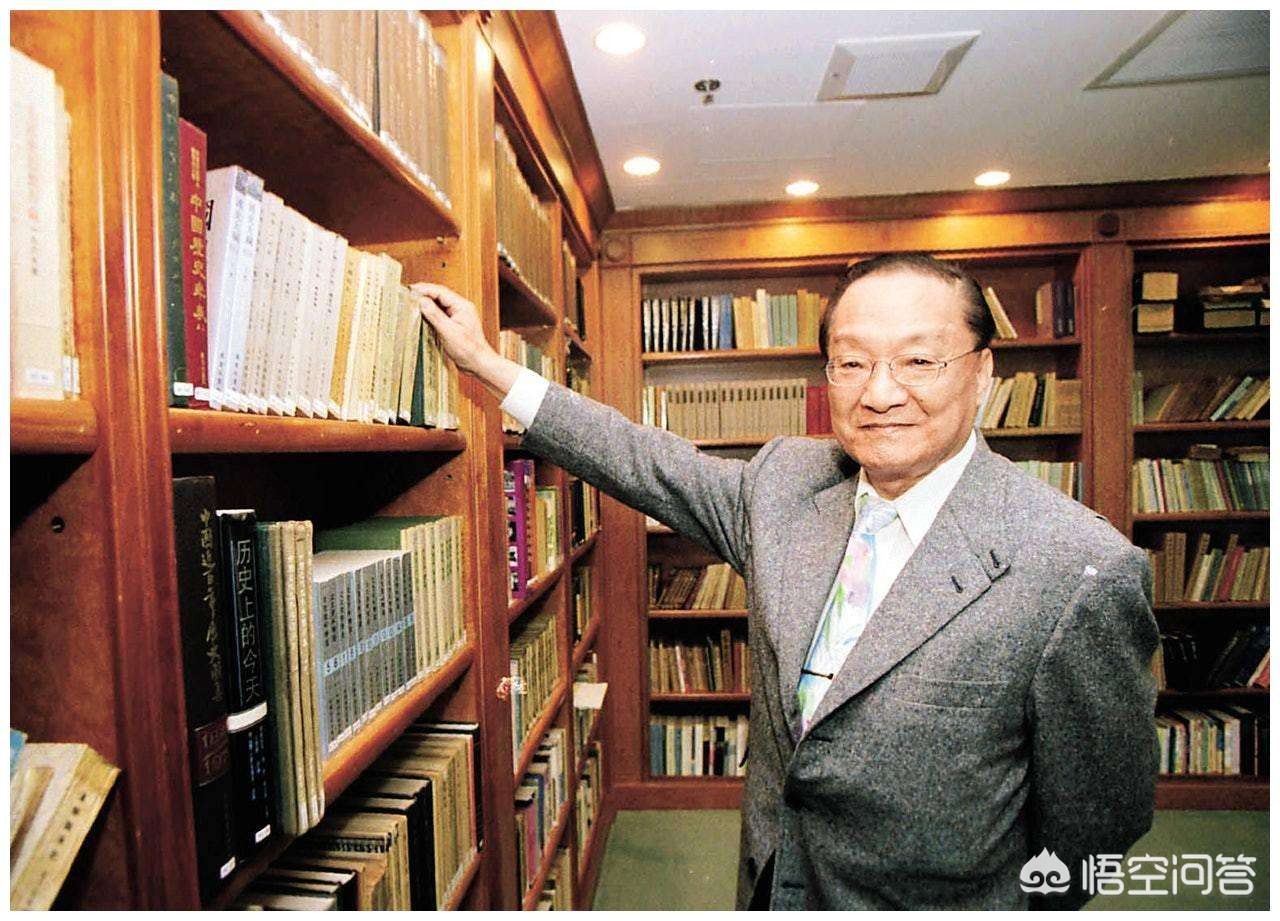声色市井的饮食男女——《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 文化
- 2023-05-16
- 160
自明代始,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步入了发展的鼎盛阶段,先后诞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四大奇书”。其中,万历年间问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位列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不仅摆脱了口耳相传和集体加工的成书模式,乃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名著,自使文人创作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而且突破了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创作传统,直接以现实社会中的世态人情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成为我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这种白话写作和写实手法,皆是《金瓶梅》自觉承接和借鉴《水浒传》的成果。除此之外,它还沿用了《水浒传》中关于潘金莲的故事情节,“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续写和再创作。相较于英雄传奇式的《水浒传》,《金瓶梅》将关注视野由波澜壮阔的人民起义斗争,转向零细琐碎的市井生活和家庭故事,将写作对象由绿林好汉转向饮食男女,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取代曲折离奇的小说情节,结合人物的成长环境和内心世界,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尤以女性描写最为出彩。而横跨两大奇书的潘金莲,在兰陵笑笑生的精雕细琢下得到了进一步演绎和诠释,生发出无尽的表现力和不朽的生命力。她从类型化走向个性化,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从英雄时代进入市井生活,从微不足道的配角升为耀眼夺目的主角,从“水浒第一淫妇”登上“千古第一淫妇”的席座。
作为“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画”,《金瓶梅》“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人间的假、丑、恶”,真实再现了当时社会中人性的扭曲、心理的畸化和灵魂的变异,对封建末期的种种罪恶、虚伪和腐朽予以一针见血的暴露,其女性形象不仅个性纷呈、活灵活现,而且具有“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典型意义。因此,在《金瓶梅》中,潘金莲虽本性依旧,但已不再是用以突显武松的概念化人物,而是一个复杂多变、饱满鲜活的圆形人物,系全书的核心所在。她精明乖巧又刁钻刻薄,凶狠毒辣又卑躬谄媚,争强好胜又敏感懦弱。作者并未如《水浒传》一般对其性格内涵和人生经历作简单处理,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较为详细的添改,通过揭示其性格形成背后的时代环境、社会背景、世俗风气和个人生命体验等各类因素,逐步浮现潘金莲畸形性格的嬗变轨迹,使之趋于合理、符合逻辑,从而弥补了施耐庵的创作缺失。
相比《水浒传》中寥寥数语的简要概括,潘金莲在《金瓶梅》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始终居于故事舞台的镁光灯之下,拥有明确的家世背景和详实的生平叙述,占据了整部小说的大量篇幅,其性格生成的基点也随之前移。若说在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于少女时代拒绝大户纠缠时,尚存一丝反抗意识和贞洁观念,那么兰陵笑笑生便将这唯一的一抹亮色洗刷得荡然无存,其淫妇生涯自幼而始,至死方终。她本是山东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因家贫丧父,九岁就被卖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百般调教,学得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描鸾刺绣、品竹弹丝无一不精,在淫靡之风的耳濡目染下深谙男盗女娼、以色侍人之道。待王招宣死后,她又被其母以三十两银转卖予张大户家,长至十八岁便出落得眉似新月、面若桃花,顺其自然地为年过六旬的张大户收用。岂知大户因与金莲纵欲过度而多添病症,为主家婆嚷骂数日,遂将她白嫁于软弱忠厚的邻居武大,方便与其暗通款曲。已为人妇的潘金莲未曾中断这种有违人伦的厮会,反之坦然顺从,以此来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物欲和肉欲,即使在张大户耗尽阳气、一命呜呼之后也难耐寂寞,整日打扮光鲜,倚门卖俏,“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儿,一径把那一对小金莲做露出来,勾引的这伙人,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扠儿难”。
由此可见,潘金莲的堕落之路从幼时便开始逐步推进,而导致其“生性放荡”的主要原因就是她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下被动接受的性教育。从王招宣悉心教导时施加的性启蒙,到张大户无耻收用后萌发的性意识,又在婚后偷情中享受到由美色带来的物质和肉体上的双重满足,触发了潘金莲潜藏的性冲动,致使她将永无止境的情欲和性欲作为毕生渴求,把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奉为处世原则。故而,当她被错配给愚弱猥衰的武大后,在婚姻生活中备受性压抑和性苦闷,以至于为达私欲不择手段,先是费尽心思地勾引武松,妄图与小叔乱伦而遭拒,而后阴错阳差与西门庆奸合,为性欲驱使不惜剪草除根、毒杀武大。至此,潘金莲的身心已然异化和畸变,沦为欲望的奴隶和帮凶。
毫无疑问,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延续了潘金莲的原始形象,并且将其“淫妇”的特性不断加以夸张、放大,由“淫妇”转为“淫妇、悍妇、妒妇和毒妇”,融美色、淫毒、阴狠、善妒和乖戾为一体。当其复杂畸形的性格基调在前期经历中初步形成之后,作者一改《水浒传》的仓促收尾,令县中皂隶李外传无端作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替罪羊,使二人侥幸逃过一劫,续写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婚后生活和爱恨纠葛,在这个奢靡无度、荒淫无耻、贪婪无厌、争斗无休的罪恶之家里,上演另一出醉生梦死的市井丑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潘金莲嗜欲善妒、淫骄歹毒的淫妇形象,使其更为复杂化、具体化和典型化。
当潘金莲被西门庆娶为“五房”后,作者主要从两方面描叙了她的欲望人生:
一是肆无忌惮地放纵淫欲。由于潘金莲对肉欲毫无自制之力,为求长期得到性满足和性愉悦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一方面,她试图霸占丈夫以成为其专属的泄欲工具,使尽浑身解数来征服西门庆,对其卖弄风骚、曲意逢迎,不但献上春梅百般讨好,而且任他醉吊于葡萄架下肆意淫乐,险些丧了性命也在所不惜,行
为之放荡正如作者所言:“蛊惑其夫,无所不至。虽屈身忍辱,殆不为耻”。①另一方面,她又无法克制自无以复加的肉欲和泛滥成灾的情欲。当意识到西门庆并非忠心不二的性伴侣时,她便伺机与孟玉楼十六岁的小厮琴童奸通,和名义上的女婿陈经济乱伦,以此来填补丈夫寻花问柳时的空虚寂寞。这种饥不择食、无视纲常的荒唐行为正是暴露了潘金莲的贪淫无度、欲壑难填,致使西门庆服食淫药过度而油尽灯枯,堂堂六尺之躯断送于潘金莲的欲火之下。待西门庆髓尽人亡后,潘金莲不顾亡夫尸骨未寒,又与陈经济乱作一处,后因奸情败露而被驱赶出家、处境堪忧时,竟也不忘与王婆之子王潮儿偷欢淫乐。早已为情欲丧失理智、蒙蔽双眼的她,最终自以为是地沉浸在对武松的性幻想中,惨死在武松的屠刀之下。
二是费尽心机地排除异己。在为一己之欲毒杀武大后,潘金莲的人性和良知就此泯灭。当她进入一夫多妻的西门府后,性欲的满足、丈夫的专宠便成了她生存的目的和手段,这种在畸形家庭中衍生出的强烈欲求,促使她开始勾心斗角、争奇斗艳的夺宠之路。先是恃宠生娇,挑唆西门庆毒打孙雪娥,在众人面前建立微信,后又嫉妒宋蕙莲,教唆西门庆迫害其夫来旺儿,逼得她险些自缢身亡,接着利用孙雪娥刺伤宋氏,终于将其置于死地。而后,潘金莲便将矛头直指母凭子贵、备受宠爱的李瓶儿。一面倾尽全力迎合丈夫的淫欲,媚惑西门庆以夺其宠。当她听到西门庆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时,“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与其百般狎戏、共浴兰汤,使西门庆欲罢不能。另一面则不择手段地削弱李瓶儿的气焰,吓死官哥儿以夺其命。由于潘金莲“平日见李瓶儿从有了官哥儿,西门庆百依百随,要一奉十,每日争妍竞宠,心中常怀嫉妬不平之气”,因而她不仅在平日话闲时针锋相对、刻意挖苦,变相地欺压李瓶儿,而且故意设计惊唬胆小的官哥儿,借李瓶儿和官哥儿好猫之心,豢养并驯练雪狮子扑食用红绢包裹的肉食,用以攻击穿着红衫的官哥儿,致使小儿受惊夭折,李瓶儿丧子惹疾,不久便血崩而亡。由此可见潘金莲心计之多、城府之深,为了追逐情欲和私欲不顾一切地恣意淫乱,殚精竭虑地扫除障碍,更是使得人丁兴旺、显赫一时的西门府最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之无愧地位列古今淫妇之榜首。
此外,作者在直接刻画潘金莲“淫、妒、毒”的同时,也从细节对比上塑造其多面性格,使其血肉丰满、跃然纸上。她既把西门庆当作宣泄欲望的工具之一,甚至在寂寞难耐时频频出轨,丝毫不顾及其颜面,又对西门庆真情一片、爱意绵绵,曾两次深夜弹唱琵琶倾诉内心情意:“奴家又不曾爱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情性儿乖”;既在众位妻妾奴仆面前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又在西门庆身边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终日恁提心吊胆,陪着一千个小心”;既在丫环面前居高自傲、使尽威风。婚前毒打迎儿,婚后折磨秋菊,或鞭打或暴晒或罚跪或耳掴,将怒气和欲火变相地发泄在幼女身上,毫无宽厚仁慈之心,又与婢女庞春梅之间建立起真挚的友谊,不但心甘情愿地帮助春梅上位,共同分享夫君的宠爱,而且在家族倾轧时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可算是全书中罕见的情真意切。因此,在潘金莲身上,集齐了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情与欲、强与弱等种种矛盾对立的性格元素,一齐构成其最为真实的人性和最为鲜活的个性,赋之以无穷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兰陵笑笑生并未将这一艺术形象从《水浒传》中简单抽离出来,乔装打扮一番便登台亮相,而是令其脱胎于畸形发展的明末社会,放置在繁琐庸常的市井家庭中,生发出崭新的个性色彩和生命活力。
然而,作为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潘金莲从诞生伊始便遭人唾骂,纵使其在《金瓶梅》中聚积着极其复杂的性格因素,蕴涵了非常广阔的阐释空间,但却始终为庸俗的性爱描写所掩盖,被“淫”字的标签所遮蔽,使之一直被钉在淫妇的耻辱柱上,备受古今文人的口诛笔伐。恰如某学者所言:“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一千个读者绝不会有一千个潘金莲”,清代文人张竹坡曾犀利点评道:“西门庆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了,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北图藏《金瓶梅》文龙批本亦声色俱厉地批判道:“写金莲之淫,亦可谓写到十二分。死期近矣,再活亦不过如此。”《第八十六回回评》这种种否定和抨击的言论,无疑显现出潘金莲形象的性格力度和审美价值,体现出作者塑造人物的高度艺术成就,突破了《水浒传》的旧有框架,创造出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又一座文学高峰。
可是,对潘金莲的一致声讨和片面攻击,也间接暴露了作者和世人狭隘的女性观,折射出封建男权社会歪曲和轻贱女性的普遍心理。兰陵笑笑生虽以市井女性为书写对象,浓墨重彩地描绘女性的世俗生活和声色世界,但却未能跳脱出男权文化的固有囹圄,依旧弹奏着“红颜祸水”的陈词滥调。由于作者身处的明末社会,正是封建主义衰落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混乱时期,传统的道德规范已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又催生了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颓败之风大行其道,没落腐败的封建社会亟需振聋发聩的劝诫之声。因此,该书着意把潘金莲当作淫邪和罪恶的化身,将其置于饮食男女的情欲漩涡中变形发酵,以极端的利己和享乐主义取代了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的观念外衣,大肆渲染其人性的腐烂和肉欲的泛滥,令其淫妇形象向极端演化,甚至畸变成了嫉妒与阴毒,由此发出“酒色多能误邦国,由来美色丧忠良”的谆谆告诫。《金瓶梅》从文章伊始便举出项羽因迷恋虞姬而自刎、刘邦为宠妾戚氏而志屈的事例,引出“虎中美女”潘金莲及其风情故事,认为“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卷终又以诗为证,谓“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恰巧昭示了作者“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的写作意旨。但这种以歪曲女性来警醒世人、整饬世风的作法,毫无疑问是受到男性话语操纵的结果,通过贬低和压制女性主体价值和个体欲望的方式来宣扬封建礼教思想,对高扬厌女主义旗号的《水浒传》作出另类的呼应和回归。
孔子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和性,作为人的本性,亦是人最基本的两大欲求。古人虽承认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满足欲望的必要性,但却更强调“乐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的重要性,主张以礼教和礼法的严格标准规范人之欲求、判定人之品性,故循规蹈矩者为“贞”,放浪形骸者为“淫”。纵潘金莲在《金瓶梅》中的人生历程,不论开始抑或结束都逃不开一个大写的“淫”字。她半生残害无辜,结果死于武松的残杀下,一生追逐肉欲,最后终于对武松死灰复燃的情欲下。这番由色而生、为欲而亡的命运轨迹显然映现了潘金莲纵情恣性的情色生涯,显现了作者匠心独运的情节设计,印证了“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的警世诫言。如果说施耐庵造就了类型化的潘金莲,那么兰陵笑笑生便成就了个性化的潘金莲,既使其形象远比之前更为鲜明、复杂和矛盾,也令其一生自此再也无法摆脱“淫妇”的原始印记,化为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