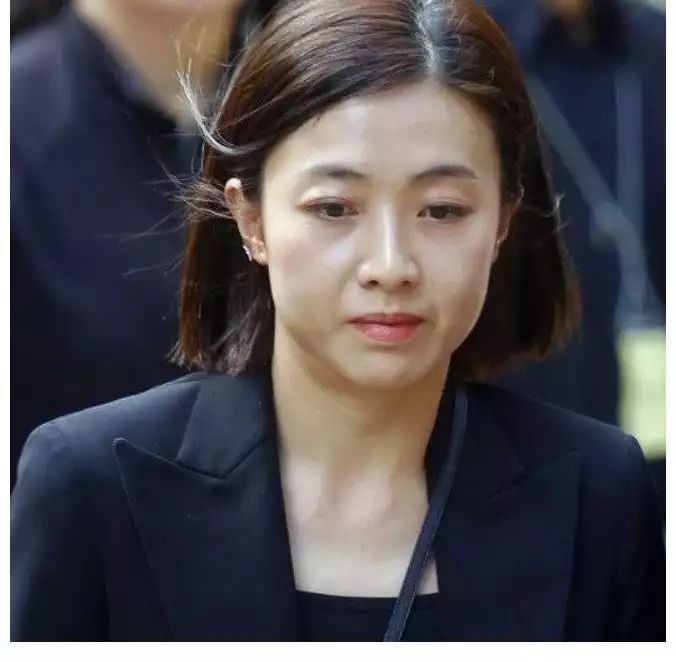【边疆时空】冯科 | 辽圣宗云中知遇张俭考论
- 文化
- 2023-07-09
- 56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冯 科
历史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讲师,主讲中国古代史、中国北方民族史等课程,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辽金元史,主要从事契丹—辽史研究。
摘 要:辽圣宗游猎云中,知遇张俭。这不仅是“一代之宝”——张俭扶摇直上的开始,也奠定了在韩德让之后圣宗、兴宗两朝汉官地位继续稳固的格局。张俭以“名符帝梦”为圣宗所知遇,反映了君臣知遇的梦兆模式在圣宗朝选贤任能和推行变革中的作用。这一现象的背后当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内涵,既包含有圣宗对韩德让权力过大、地位过高的排斥心理,也是圣宗在为汉化改革的有序推行而储备人才,同时又有汉文化对圣宗乃至契丹社会的影响等因素。
关键词:知遇;梦兆;张俭;辽圣宗
张俭作为辽代圣宗、兴宗两朝具有代表性的汉官,科举出身、履历丰富、为政有声、官高位显。《辽史》论曰:“张俭名符帝梦,遂结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两朝,世称贤相,非过也。”君臣知遇的范例,有辽一代为数不少,然而包含梦兆因素的圣宗知遇张俭的情形却是少见。以梦兆为先导的知遇模式,出现在辽代的社会中,当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探讨其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对于了解辽朝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是有益的。
一、辽圣宗知遇张俭的异梦
《辽史·张俭传》记载:“故事,车驾经行,长吏当有所献。圣宗猎云中,节度使进曰:‘臣境无他产,惟幕僚张俭,一代之宝,愿以为献。’先是,上梦四人侍侧,赐食人二口,至闻俭名,始悟。”此圣宗异梦的记载不见于其他史料,但罗继祖和陈述皆认为“当别有所据”,“另有源据”。其实根据《张俭墓志》的相关记载,还是可以发现在张俭的人生中有着兆应帝王梦的奇幻色彩。其铭曰:“钓国得璜,干君负俎。内秉鸿枢,中藏鸾渚。赤符肇应,绿绶载纡。桓圭申命,史笔专书。”此段文字中前两句分别用了姜尚和伊尹的典故,“钓国得璜”是指姜尚于渭水垂钓为周文王所知遇,“干君负俎”是指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而为商汤所知遇。虽然铭文中并没有明确显示君臣知遇中的梦兆因素,但是,无论是文王知遇姜尚,还是商汤知遇伊尹,都流传着梦兆的故事。唐代李白有诗曰:“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即言姜尚垂钓皤溪(渭水支流)事和伊尹梦应汤命事;唐五代至宋初的陈抟有诗曰:“渭水飞熊还人梦,管教重日照前程。”即言姜尚垂钓渭水,梦应飞熊事。无论是李白诗,还是陈抟诗,都说明唐宋时期所流传的商汤知遇伊尹、周文王知遇姜尚的典故,已经包含了梦兆的因素。《张俭墓志》借用具有梦兆因素的君臣知遇典故来铭赞墓志主人,或别有深意。
再看后文“赤符肇应,绿绶载纡。桓圭申命,史笔专书”,亦有深意。虽然“赤符肇应”可以理解为是指墓志中提到的张俭“初下帷读书,栖毫假寐。仿佛见人谓曰:‘天上一枝桂,人间三品官’”,“桓圭申命”可以理解为是指《张俭墓志》中所言“论者曰:官逾一品,爵首五圭”;但是“桓圭”确实是五圭之首,而“绿绶”却不是三品官所能受用的。当然文学性的语言允许模糊性的指称,何况墓志中也提到张俭官逾一品。然而,由于“赤符”作为代指帝王受命的符瑞,不能不让人认为墓志作者在暗示“赤符肇应”是指“张俭名符帝梦”一事。如果说文学性的语言允许以“绿绶”对应“人间三品官”,那也应该允许“赤符肇应”有一语双关的内涵。如果说“赤符肇应”与圣宗异梦和张俭之名有关,那为什么墓志中不明确提出圣宗梦俭名一事呢?这或许是因为有关圣宗皇帝异梦一事,不应该出现在臣子墓志之中;也可能是因为圣宗知遇张俭一事有着比较复杂的因素。
二、辽圣宗知遇张俭的时间
圣宗知遇张俭之际,张俭尚为云州幕官。《张俭墓志》记载张俭为官经历甚详,却没有记载张俭为官云州幕中。向南认为由顺州从事调云州幕官,李桂芝认为先为云州幕官后试顺州从事,二者的共同点是:张俭为云州幕官当是在为官顺州从事前后。如果分析《张俭墓志》所记,还可得出张俭是在其他时段为云州幕官的结论。
《张俭墓志》记载:“统和中,一举冠进士甲科,一命试顺州从事。署棘寺丞,以谳狱调范阳令,以字民迁监察御史。供职行在,簪笔以肃朝宪。补司门外郎,赞画留幕,履珠以观民风。”其实这段文字如下断句,或许更为合适:“统和中,一举冠进士甲科,一命试顺州从事。署棘寺丞,以谳狱;调范阳令,以字民。迁监察御史,供职行在,簪笔以肃朝宪;补司门外郎,赞画留幕,履珠以观民风。”“一命试顺州从事”当是指张俭第一次被任命官职,就以顺州从事作为锻炼。之后是代理大理寺丞、调范阳县令。以监察御史供职行在是有可能的,《辽史·营卫志中》记载皇帝捺钵,“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之后说张俭“补司门外郎,赞画留幕,履珠以观民风”,“留幕”“履珠”明显是指张俭为幕僚的意思。然而,司门外郎是尚书省司门司副官,显然是中央朝官,不可能是幕官;但是,张俭如果是以幕职的身份观民风要比以中央朝官的身份更为合适。“辽朝的南面官制基本上是继承唐制”,而唐代官制中幕职带朝衔或宪衔始于开元后期已为石云涛所论证。尚书员外郎即为节度副使、行军司马、判官、节度掌书记、参谋、观察使支使等幕职所带朝衔。辽代《宋匡世墓志》署:“外甥中京留守判官、朝议郎、尚书吏部郎中、赐绯鱼袋王景运撰。”可见王景运即以中京留守判官的幕职带尚书吏部郎中的朝衔。《刘承嗣墓志》署:“子耸,齐国王府记室参军、朝议郎、尚书司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冯圮撰。”也可见冯圮即以幕职带尚书司门员外郎的朝衔。张检很有可能是由监察御史人云州幕,以幕职带司门员外郎的朝衔。因此说张俭为云州幕官是在补司门员外郎时段,当有可能。并且《辽史》说张俭在云州为圣宗所知遇之后,“由此顾遇特异”。如果说张俭调云州幕官是在顺州从事前后,显得不太合理,因为无论是大理寺丞还是范阳县令,乃至监察御史、司门外郎,都不能称得上是“顾遇特异”。然而,张俭于司门外郎之后所历官职,当可称得上是“顾遇特异”。比如,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服阕之翌日,授礼部郎中、知制诰、直枢密院”,“开泰元年(1012年),迁政事舍人、知枢密直学士。二年,正授枢密直学士、同修国史。三年,加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诘”。开泰三年(1014年)“夏六月,授宣政殿学士、守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论思秘殿,参预中堂。朝廷能之,遂掌军国。冬十月,授枢密使,加崇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特赐翊圣佐理功臣”。之后更有加政事令、左丞相等职官。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记载:“由此顾遇特异,以为政事舍人。”显然是以张俭为官政事舍人作为“顾遇特异”的开始,这或许是因为毕沅所据史料不如《张俭墓志》详细。根据张俭于统和二十九年已经“诏充贺南朝皇帝生辰国信副使”。可知,此时已经为圣宗所顾遇。因此,以统和二十九年“服阕之翌日”作为张俭“顾遇特异”的开始,似乎更为妥当。《张俭墓志》在“补司门外郎,赞画留幕,履珠以观民风”之后,紧接着写道:“鹏翼张以弥天,抟扶摇而直上。”似亦是说张俭在补司门外郎之后,平步青云,可谓“遇主则鱼纵大壑,戴君则鳌冠灵山”。可见,张俭是在补司门外郎之后为圣宗所知遇,由此而“顾遇特异”。那么圣宗猎云中当是在张俭为官司门外郎时期,统和二十九年“服阕之翌日”的“顾遇特异”之前。又据张俭是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始丁先太傅忧,因此圣宗云中知遇张俭的时间或更在1009年服丧之前。
张俭是在统和十四年(996年)“举进士第一”,此后历任官职分别是顺州从事、棘寺丞、范阳县令、监察御史、司门外郎等。根据“辽朝官员任职有期,一般为三年”的惯例,若以三年一迁转,张俭在中进士当年即试顺州从事,则应在999年署棘寺丞,1002年调范阳县令,1005年迁监察御史,1008年补司门外郎为官云州幕中。以此来看,恰也在1009年张俭丁忧之前。再査《辽史·游幸表》有载:圣宗于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十一月猎于桑乾河。《辽史·圣宗本纪五》亦记有统和二十三年十一月“观渔桑乾河”,“二十四年(1006年)春正月,如鸳鸯泺”。鸳鸯泺位于云中之北的奉圣州内,桑乾河上游流经弘州、奉圣州等地,皆近于云中。可见圣宗曾于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十一月到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正月游猎于云中一带。考虑到“辽朝官员的确存在大量的非‘秩满’(三年)迁转现象”,若张俭在补司门外郎之前,并非都是“秩满”而迁转,那么在1008年之前的两三年时间里,即1005—1006年圣宗在云中一带游猎之际,张俭或已补司门外郎为官云州幕中了。更何况,《张俭墓志》所言张俭“三年泣血”的服丧期是指从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丁父忧开始到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复入朝结束,似说明“三年”期并非实实在在的满三年。相应地,从996年张俭初为官到补司门外郎,即使是“秩满”而四次迁转,也并不一定要经历完整的12年。因此,1008年只是张俭为官云州幕中的至迟年份。
综上所述,张俭在996年中进士,以顺州从事人仕,此后经历了四次迁转,在补司门外郎之际为官云州幕中。根据辽代的官员任期状况,张俭在云州幕中为官的时间当不晚于1008年,结合圣宗猎云中的时间,或是在1005—1006年为圣宗所知遇。
三、辽圣宗知遇张位的历史背景
1005—1006年圣宗知遇张俭之际,契丹一辽政权的最髙统治核心应当是以承天太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为首。汉官韩德让在承天太后等人的支持下执掌朝政,推行汉化改革。以韩德让为代表的汉官具有较大的权力和较高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契丹官员的权力和地位。汉族人为契丹北院枢密使者,有辽一代只一人,即圣宗朝时期的韩德让;《辽史》所见的圣宗朝契丹南院枢密使,皆为汉官;由后族和皇族世选的北南府宰相,在圣宗朝亦有汉族人(室昉、韩德让、刘慎行、邢抱质等)担任的现象。甚至出现朝中一度汉官为盛的状况,在统和十七年(999年)九月耶律斜轸去世至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三月韩德让去世的这段时间里,有韩德让总二枢府事、韩德让和邢抱朴曾为契丹北南院枢密使,邢抱质曾为南府宰相、韩德让为中书省大丞相。此际,枢密院、中书省皆以汉官为主管官员,且南府宰相亦曾由汉族人充任,可以说汉官在朝中的权力地位相对稳固,大有超过契丹官员的趋势。朝中汉官地位的提升和稳固,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利于汉官的升迁发展,也影响了圣宗对汉官的态度,这样的局势为张俭被圣宗所知遇奠定了主客观上的条件。此外,韩德让权力地位的隆盛,也对圣宗有所影响。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十二月,辽宋签订澶渊之盟,“是月,班师。皇太后赐大丞相齐王韩德昌(即韩德让)姓耶律,徙王晋”。又于统和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已,诏大丞相耶律德昌出宫籍,属于横帐”。韩德让总二枢府事,官拜大丞相,赐姓耶律,隶属横帐,使其权力、地位、名望达到了顶峰,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圣宗的权力空间,甚至其身份地位有凌驾于圣宗之上的趋势。史书中圣宗以父事韩德让的记载,恰也说明了韩德让地位之尊。然而,这种情形并不一定是圣宗所愿意的,从后来圣宗赐韩德让名耶律隆运即可看出。
《辽史》记载: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夏四月甲子,葬太后于乾陵。赐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运”。赐名隆运之日正是萧绰下葬之日,这当是圣宗耶律隆绪的赐予。那是否可能出于承天太后的遗旨呢?答案是否定的。《耶律隆祐墓志》记有:“公讳隆祐,字道宁……金昆集莫大之勋,正调殷鼎;玉季树不朽之业,俱陟韩坛。我皇朝追彼职官,敢有夷念。兹忠孝萃于一门,故颁之以敕书,赐之以国姓。乃连御署,得系皇亲,今氏归耶律,则斯之谓欤?”此耶律隆祐即为韩德让弟德颗(德凝),明显韩德颗“今氏归耶律”是因为金昆玉季之勋业,忠孝萃于一门而赐国姓、连御署。韩氏一门昆季里忠孝的代表当是韩德让,可以说是因为韩德让被赐名“隆运”才使韩德颗被赐姓名耶律隆祐”。则耶律隆祐赐姓名的时间当在韩德让赐名隆运之后,而耶律隆祐于统和二十八年冬壬戌日去世。似乎可以推测:韩德让赐名耶律隆运之后不久,韩德颗去世,圣宗念韩氏一门忠孝,于是也赐韩德颗连御署为耶律隆祐。这起码表明非韩德让一人连御署“隆”字,若是承天太后遗旨,当不至于殊荣二人。即使是承天太后遗旨殊荣于韩德让一人,圣宗也让此殊荣泽及韩德颗,当有其深刻用意。圣宗以赐名“隆运”连御署的殊荣抬高韩德让的名誉,实是以此为名目兄事韩德让,而赐韩德颗名“隆祐”更是为了突出“兄事”的用意。《耶律隆祐墓志》中说:“皇帝以手足兴怀,柱石挂念,遽闻捐馆,寻示辍朝,命星使以临丧,赐天书而恤寡。”明显圣宗要对隆祐表示出手足的情分,其效果也是明显的。《耶律隆祐墓志》铭曰:“邦国宗枝,皇王昆季。”圣宗借韩德颗去世之机,大行兄弟之情,让时人明白耶律隆祐为耶律隆绪之兄弟,那么耶律隆运也当为耶律隆绪之兄弟。
统和二十八年赐名“隆运”是圣宗在萧绰去世之际,以玉谱联名的殊荣抬高韩德让地位,通过以同样的殊荣赐予韩德颗,表示出兄事韩德让的态度。《契丹国志》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均有圣宗父事韩德让的记载,《辽史》虽无相关记载,但也绝不是以兄事德让。由于圣宗皇后——齐天皇后为韩德让的外甥女,因此或可以舅父事之。圣宗赐韩德让名“隆运”,与其说“兄事之”是殊荣,倒不如说是借此殊荣降低了韩德让的辈分。降低韩德让辈分恐怕是圣宗对以往“父事”的反弹,这种反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韩德让的权力之盛、地位之隆,已经影响到了圣宗的君主权力和地位。这种君臣关系是圣宗所不能长期接受的,因此在葬承天太后之日,圣宗即通过赐名的方式,表达出“兄事”韩德让的用意,从而纠正以往“父事”的君臣关系模式。由此可见,圣宗与韩德让的君臣关系模式并非圣宗所理想的,这样的君臣关系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圣宗另寻更为适意之臣。
四、辽圣宗知遇张俭的历史内涵
云中知遇张俭作为圣宗的个人行为,或许有着深层次的内涵。既然圣宗猎云中之时张俭已经任过朝官监察御史,曾供职行在,并且张俭是在“统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那么,作为当年状元的张俭之名是不应该不为圣宗所知晓的。圣宗知遇张俭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事,不仅仅是巧合,里面有着圣宗或张俭等人的主观能动性。
《张俭墓志》铭曰:“钓国得璜,干君负俎。”明显是说张俭一方面是被动地“钓国”,一方面是主动地“干君”;一方面是主动想办法创造条件(负俎)地“干君”,一方面是已经得知臣“佐检”君“来提”(得璜)才被动地“钓国”。这好像是说圣宗知遇张俭一事,是张俭主动创造条件为圣宗所知,并知道会为圣宗所用,其主动和被动是统一的。即使圣宗知遇张俭纯属偶然,但至少也可以说明圣宗久望贤才如文王,张俭得遇明主如太公。虽有韩德让等人辅助,但圣宗另寻贤才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来不至于人才断层,二来另寻更为合意之臣。圣宗于韩德让更多的是既成事实下的尊重和倚仗,很难有君臣知遇的水乳交融。因此知遇张俭的圣宗异梦一事,是圣宗潜意识里排斥与韩德让式君臣关系的表现,或许也是久在心中衡量张俭之名(“四人侍侧,赐食,人二口”指“俭”字)的结果。虽然圣宗在云中知遇了张俭,但并没有像文王知遇姜太公那样“载与俱归,立为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那么迫切的形势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圣宗当时并没有文王那样的政治自由。没有政治自由,一方面是因为辽朝此时的官员升迁任命已有定制,另一方面是承天太后和韩德让对君权的制约。直到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张俭服丧期满方为圣宗所“顾遇特异”,这时承天太后已经去世,圣宗的君权相对加强,能够独立自主地建立更为融洽的君臣关系模式。
当然,圣宗异梦对韩德让的排斥,不仅有其个人原因,也有平衡契丹官员与汉官权力的考虑。圣宗知遇张俭,张俭能够在仕途上不断发展,一方面是由汉官在朝中的格局地位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圣宗重视汉官的结果。与承天太后主政时期相比,圣宗主政时期汉官权力有所减弱、地位明显下降,契汉官员的权力地位再度平衡。特别是韩德让去世之后,北枢密院重新归契丹官员主管,保证了圣宗朝后期北南院枢密使分别为契丹官员和汉官的格局。圣宗削弱汉官的权力,起用契丹官员,是保证政权中契丹官员主导地位的需要。然而圣宗并没有忽视汉官在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依然重用汉官为其改革服务。圣宗朝后期重用汉官张俭、继续推行汉化改革,无不显示着汉文化和汉官对耶律隆绪的广泛影响。
因此,知遇张俭的“圣宗异梦”既反映了圣宗排斥与韩德让式的君臣关系模式,又反映了圣宗对寻访汉臣、推崇汉化的渴望。这与圣宗深受汉文化影响有关,《辽史》记载:“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可以说,汉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君臣知遇的梦兆模式,开启了圣宗的云中之行。
【注】文章原载于《宋史研究论丛》2022 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边疆时空】范传南 | 清代中前期北疆治边政策及其影响
【边疆时空】陈庆元 | 东海擒倭与董应举《海石铭》——纪念东沙大捷四百周年
【边疆时空】李红阳 | 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
【边疆时空】张保平 | 海上犯罪的特点与海上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