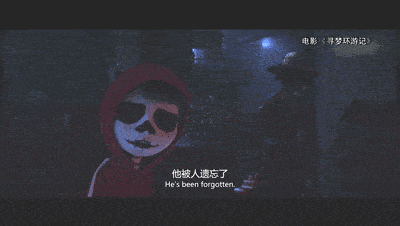在父亲的田园诗里冬眠
- 情感
- 2023-09-19
- 125
这是父亲给我上的一堂人生早课。
那时的我还在一片多彩的童话世界里,一天到晚从不问事,困了睡,醒了就在香瓜地、丝瓜架下,在父亲的田园里疯跑上一气,常被黏黏糊糊的蜘蛛网粘了一脸。生气的我像勇猛的唐吉诃德,把高粱秆儿当成一柄长剑不停地挥舞着,挥向蜘蛛。父亲笑呵呵凑过来,饶有耐心地劈开最前端的高粱秆儿,支撑出一个三角形来,在蜘蛛网上滚来滚去,蜘蛛的“辛辛苦苦”就结在了高粱秆儿上,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地念着“咒语”:嘛离,嘛离,落落,落在干草垛,一落七八个。“嘛离”是蜻蜓的别称。伸出的食指高过头顶,等待蜻蜓落下来,用网来黏捕蜻蜓。童年的蜻蜓非常好看,有诱惑人的蓝尾蜻蜓、红尾蜻蜓、细尾水蜻蜓,还有神秘而灵活的大眼睛。
小小的高粱秆儿,粘满了童年的无限乐趣。记忆里,那个胖嘟嘟的孩子整天像风一样无忧无虑地奔跑。后来学到“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使我深信不疑,诗人高鼎写的就是我。
我很骄傲地说,我小时候糊过风筝。父亲是个大孩子头儿,他用细细柔柔又有着韧性的竹坯子做骨架,细铁丝足够细,以减轻风筝的自重。等长的竹坯子搭制成一颗五角星,用细铁丝捆牢,浆糊把褐色的脆响的牛皮纸来回地糊在竹坯上,线分五股,系在五个角上,一个简易的风筝就做成了。
我们拿起心爱的蜡笔,在风筝上画满了爱的色彩,画满了一个个美好的愿望。一只风筝带着我们的愿望翱翔在蓝天上。我们兴奋地奔跑,兴奋地跳跃,仰望着高高飘扬的风筝,心情无比舒畅。
我们那时放风筝唯一不同的是在冬天,而不是在春天,在朔风凛冽的莲花泡儿的冰面上、雪地上,茫茫大雪覆盖了整个莲花泡儿,我们不怕冷,淌着清鼻涕,穿着没有外套的夹袄,袖头泛着油光,光着脑瓜儿,不顾一切地跟着风筝奔跑。偶尔被雪绊倒了,起身后顾不上抖落身上的雪,继续哈着白气奔跑。我们轮番拉着风筝长长的细线,像牵着一份无限美好。风筝就是我们飞扬的心。
夏天的田园是碧绿的海。难忘的是那片风过碧浪涌动的黄豆地。除草是我最讨厌的农活,唯一的动力就是黄豆地里的蛐蛐叫,一声声,像满心诗意的召唤。我常常偷懒,父亲不以为然。偷懒耍滑又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把除草时间用来捉蛐蛐,而自己分得那垄草,早被父亲一带而过地除尽了。
悠闲地唱着童谣的蛐蛐和一颗装着世界的露珠,达成了一个美好的童话协议。每一只蛐蛐都是跳高冠军,我看见那只从父亲手心里逃出来的蛐蛐,倏地一闪,就轻而易举地跳到水稗草的叶片上,晃动着碧绿的草身,一颗露珠在另一侧略低矮的草叶上,映衬着一只晶莹的蛐蛐。两只蛐蛐摇啊摇、压呀压,摇曳着胜利的喜悦。
一棵碧绿的跷跷板,在夏天海洋里,隐藏了自己,撬动着夏天的趣意。它们完全没有借助风力,在豆秧下面,在海浪的下面,用自身的自重,抒写着夏季悠然的诗意。
一棵水稗草就是一个诗意十足的跷跷板。
秋天的晚霞最美,像一片片轻盈的羽毛,色彩由白变成炽热的红,不变的是一种人间少有的纯粹。人间所有的修辞,即便捻断所有的胡须,也描绘不出晚霞的色彩与纯度。
站在晚霞的下面,一纸剪影,落在夕阳的深处。
那是父亲的晚霞吗?问得自己一脸的泪花。心无杂念,是童年的,水稗草上的,和蛐蛐压跷跷板的那颗露珠,从眼角里滚落出来。那是诗意的人生四季,每个人都会在西风紧紧裹挟的秋意的时间里,感受诗意的温暖与秋凉。
秋天是人生最通达的季节,清澈、高远,所有的一切都在秋天里洗彻。
天,长高了,空旷了。霜,费劲力气几次降下来,完成色彩与空间的蝶变。翠绿变成了金黄,变成了赤红,继而大地开始了原始般的空旷。童年的居园,所见所有的,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所有的繁茂无一例外归于萧索,所有的萧索不知何时又始于繁茂,生命是一条藏着生机与萧索的抛物线,跌宕起伏。来是偶然,去是必然,所有的如意与烦恼,将会在秋天得到释怀。
干瘦的父亲掉光了牙齿,连同语言,还有他曾经苦口婆心的劝诫,一起在秋天掉光,杳无踪迹。此时的他,像一个时光锻造出的哑巴,成了听我们的、看我们的、既熟悉又陌生、让我心疼的一个老人。记忆里的那个人,他还会做风筝,还会领着我们拔草、捉蛐蛐。我常常沉浸在那片潮湿的记忆里,闭上眼睛,开始了冬眠,那些美好的记忆宛若一首首田园诗纷至沓来。
□朱宜尧